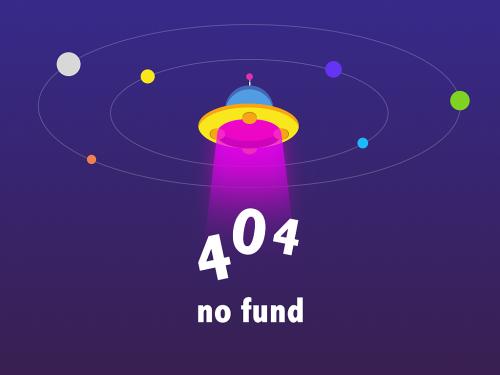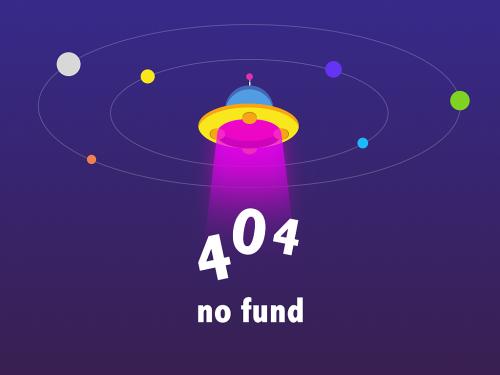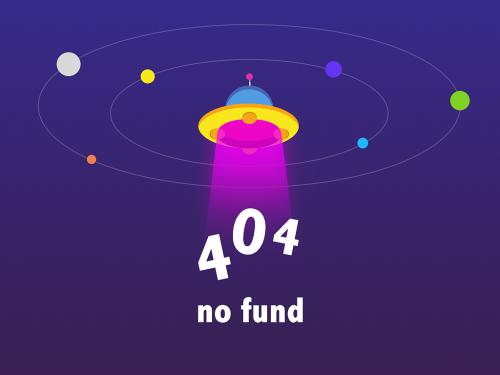法律规则的含义十篇-pa视讯
时间:2024-02-10 17:55:10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1
一、什么是法律释义
(一)法律释义的概念和特征
世界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文法的产生是法律解释的前提。从法律解释的主体及其解释的法律效力观察,法律解释可分为正式法律解释和非正式法律解释;两种法律解释形态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借鉴吸收、相辅相成。两者存在共性,均具有阐明法律意旨和促进法律实施等实践品格,同时也存在差异性。正式法律解释具有法定性和主导性,往往利用其主体的权威地位,积极吸收非正式法律解释的养分、甚至直接将其明确为正式解释。古代中国皇权,不仅直接组织律学家注释法律,如《唐律疏议》(具有法律效力),也积极吸收法律注释作品的养分;在西方的古罗马, 经君主批准的职业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创制法律的形式。与之相比,非正式法律解释则具有服务性和相对独立性(除律学家学养深厚、立一家之言外,律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如明朝律学家王肯堂撰写的《律例笺释》,对明清时期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式法律解释是指有权主体对法律法规(即法律文本)需要解释的部分这一解释对象、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也称有权解释、法定解释(以下简称法律解释)。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出现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明确适用法律依据时,可实施法律解释。按照我国法定解释主体,正式法律解释又可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解释。非正式法律解释是指有权解释主体或法学学者对法律文本逐条所作的解释,因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称学理解释。非正式法律解释的主体,主要包括立法工作机构、学者、司法、行政部门四类;其中,立法工作机构、行政部门和学者的相关实践较多。本文以下所称法律法规释义,主要指立法工作机构的法律法规释义(以下简称法律释义)。其中,地方立法工作机构对其制定的法规进行的释义,称为地方性法规释义。
法律释义与行政部门释义、学者释义同属非正式法律解释,三者都具有抽象性(多属一般性抽象论述)和论理性(侧重对法律条文的理论构成的解释)。三者也具有相异性,学者释义具有评价性,往往借助释义评价现行法的得失和提出法律修改建议;行政部门释义从执法角度出发,侧重对行政系统内部的学习与培训,具有内部的指导性和外部的引导性,但其释义撰写要基于法律释义;法律释义则因其解释主体的性质和地位而具有对内、对外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二)法律释义的要素
法律解释的要素可概括为“五要素”——主体、对象、目标、方法和效力。法律解释的主体、对象和效力,上文已交代,其方法将在下文论述。“文本特定的含义是确定的,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变动的,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单位、某个情景或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指解释主体透过法律文本这一“含义”媒介、所要探知和阐明的法律“意义”(即法律意旨)。但法律意旨究竟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主观意旨, 还是存在于法律规范中的客观意旨, 法律解释学以法律解释的目标为中心议题,出现“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对峙,其实质反映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之间的矛盾。11~19世纪的西方,先后出现的注释法、后注释法和概念法等学派以“主观说”为主流;20世纪至今,历经目的法学、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等学派构成的“自由法运动”,目前学界以“客观说”为主流。“主观说”认为, 法律解释的目标应当探知立法者意旨,而立法者的意旨是可借助立法文献得以探求的历史事实,由此拘束司法审判,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客观说”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就与立法者分离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但内在于法律规范中的意旨因社会变迁而变化, 由此产生了法律解释包括“法官造法”的需求;法律解释的目标应当探知法律规范的当下意旨,保证法律的妥当性。
比照法律解释的要素,法律释义的要素也可概括为“五要素”——主体、对象、目标、方法和效力。其中,法律释义的目标,应采“主观说”,即对文本含义和立法者意旨的阐明;其效力则为软法上的实效,体现为上位法释义对下位法的制定、释义和法律法规适用具有“体制内”拘束力,对“守法者”(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教育引导的说服力。
二、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的必要性
(一)紧密衔接法规制定和法规实施的需要
地方性法规释义具有软法功能,可充分发挥其统一立法旨意和教育引导等作用,以保障法规的正确实施。对“立法人”而言,是一次立法经验的再总结、立法成果的再巩固,一种软法的创造;对“适用者”和“守法者”而言,则是一盏指路的明灯。
(二)为实施地方性法规解释和较大的市的立法提供重要参考
地方性法规释义对有关条文规定已有明确阐释的,一般不需进行法规解释;需要法规解释的,也应充分考量地方性法规的相关释义。
(三)促进地方立法工作机构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将减少立法数量和提高立法质量,并完善配套工作。尽管立法法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白皮书等规范性文件未明确要求,但法律释义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决定其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地方立法配套工作。
三、地方性法规释义及其配套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客观制约问题。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前,地方立法任务繁重,立法工作机构力量不足,且对释义配套工作研究和积累不够,难于及时配套释义。
二是思想重视问题。未能适应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这一新形势,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较少,尤其较大的市几乎没有开展该项工作;未能充分认识法律释义的价值和作用,有的甚至认为此项工作可有可无,地方立法工作机构普遍未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规范制度。
三是实质把握问题。具体体现为:对法律释义的要素和特征等把握不准确,工作中容易与法律解释相混淆;释义名称不规范,有的称释义,有的称释义及实用指南,有的称解读或讲座,等等。
四、建构地方性法规释义及其配套机制的要点
(一)掌握法律释义的方法
法律释义与法律解释的渊源和异同,决定了两者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存在交集。
1.吸收法律解释方法的有益成分
按学界通说,广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价值补充和漏洞填补三种。其中,按是否以法律文本通常语义为标准,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又可分为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该方法可分为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解释五种方法;其中,体系解释又包括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和当然解释等四种方法)。文义解释是以通常字面含义和语法规则来明确法律文本含义的方法;论理解释则不限于法律文本字面含义,而是综合考虑法律条文之间关系、立法精神等进行解释的方法,但其仍然在条文文义的预测可能性和“射程”之内。漏洞填补俗称“法官造法”,是指因立法者的无意疏忽、未预见或社会变迁,出现法律应规定而未规定事项,则应由“适用者”(包括“司法者”)予以填补。价值补充是对不确定概念(如民法上的显失公平概念)和概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的方法,介于狭义的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两种方法之间。
依日本学者加藤一郎的观点,法律规定是个框,在其中心则含义清晰,至其边缘则渐次模糊,在框之模糊地带则存在文义复数解释的可能性。解释法律时,诸方法运用存在“序位”关系:一般以文义解释为主;出现复数解释情形时,以文义解释优先,次之为论理解释;解释结果出现相互抵触时,继之以利益或价值判断,作为解释结论[2]。
价值补充和漏洞填补显然是一种“适用者”的视角,而狭义的法律解释尤其是文义解释则是一种“立法者”和“守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视界交融”。因此,文义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也是基于“立法人”(即立法工作机构中的法律人和释义者,与我国人大代表制度下的“立法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视角的、法律释义的基本方法。
2.建构法律释义方法
法律释义自身的性质、特征和要素及其与法律解释的关系,决定了其基本方法是文义解释方法。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
(1)按照通常语言文字的含义和语法规则,阐明法律法规的具体含义。法律释义要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范实施, 力求简洁、明晰。
(2)按照法律专业术语和立法技术规范的特定含义,阐明法律法规的含义。法律专业术语俗称“法言法语”,是在法律规定中表达特定概念及其内涵的语言, 为法律人所熟知但不同于通常语言含义。为此,应遵循特殊语言优先于通常语言的解释规则。如“善意”这一概念的法律含义是不知或不应知,而非日常意义的“好意”。行政强制法(2011年公布)第九条在列举了四类行政强制措施后,又在其第五款规定“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在立法技术规范属于兜底性条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编写的该法释义,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实践中行政法规还规定了四类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本法要为行政法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留有空间”。
(3)按照“法律的意义脉络”和具体语境,阐明法律法规的含义。各民族的语言都或多或少存在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的现象。要明确某个概念或条文的含义,需要结合相关条文之间关系和具体语境等进行释义。“由上下文脉络可以确定某段文字应作何理解,同样的,法律的意义脉络也有助于个别字句的理解”[3]。如《广东省工伤条例》(2011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工伤康复”概念,因前面规定了“职工经治疗伤情稳定”的前提,主要是指“职业康复”,即在对发生工伤职工的救治医疗结束后,通过运用康复技术和设施,尽可能恢复和提高工伤职工的肌体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和职业劳动能力,以促进其回归社会和重返适合本人能力的工作岗位、提高其生活质量为目的;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康复条件”中的“康复”概念,因前面规定了“工伤职工因医疗条件所限需要转院治疗的”前提,主要指“医疗康复”,是运用临床医学的手段、方法,为患者疾病治疗提供康复服务,以改善工伤职工的肌体功能和为其职业康复等创造条件为目的,属临床医学范畴。
此外,建构法律释义的方法,还应汲取其他法律解释、哲学解释和中国古代律学等学科及其方法的理论资源。如吸收法意解释基于立法文献探知立法者原意的阐释方法;汲取哲学解释方法的有益成分,如上文所举美国文论家赫施对法律文本“含义”和“意义”的区分。
(二)把握地方性法规释义的基本原则
法制统一和地方特色相结合原则。地方性法规的释义既要避免与上位法的释义相抵触、重复,也要把握自身释义的重点和特色。
文义解释和其他方法相结合原则。从法律释义的要素和发展渊源看,文义解释是其基本方法,但亦存在借鉴法律解释、哲学解释等方法而建构的其他法律释义方法。如遵循解释学循环原理,注重对法律规定的局部与整体理解相结合的体系解释方法等。
公开和普及原则。按照法治原则,释义应以地方立法工作机构或释义撰写小组名义在地方立法pa视讯官网公布,便于公众获取和理解。
(三)把握法律释义的构成要件
法律释义的形式要件,根据法律释义的要素和特征,结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围绕近五年来制定或修改的法律所组织编写的部分释义进行比较分析,法律释义的一般要件为编写说明、条文释义和附录三部分组成。(1)编写说明为编者对编写释义目的、内容和意义等的简要介绍,多以序、前言、后记和导读等形式体现。根据是否作者自己所作,序分为自序和他序;根据处于书的目录和主体内容前面还是后面位置,序可分为前言、导言和后序、跋等。导读则是对全书内容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述。因此,编写说明名称可规范为前言。(2)条文释义包括条文主旨和条文具体释义两部分。(3)附录包括所释义的法律法规文本及上位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本、立法文件及立法参考资料和编写参考资料(目前大部分现有法律释义未附参考资料来源,尽管释义不需如论文般加注,但应附上参考资料,以尊重有关作者的贡献)等。特殊要件,如条文释义部分,根据法律自身特点,还可设有立法背景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起对照、查找作用)。
法律释义的实质要件,是对法律规范含义的阐明,即依照立法技术规范的结构顺序和法律释义的形式要件,对每一条条文(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形式)具体含义的阐明。法律文本的立法技术规范结构,一般由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内容构成大致有个范围,如总则部分包括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基本的权利(力)/义务(责任)等。法律释义的形式要件中,条文主旨释义是对法律法规每一条条文主要旨意的概括性阐释,犹如条文具体释义的标题,起画龙点睛作用。如法律法规第一条的条文主旨释义,一般即是“关于某某法立法目的和依据的规定”。条文具体释义是条文释义的主干部分,其实质是运用恰当的释义方法和结合法律要素分析,对条文具体含义,包括对条文规定的概念、原则、规则、具体制度等的阐明。
传统法律要素为“三要素说”,包括概念、原则、规则。本文认为基于法律规定的立法视角,法律要素可扩展为“四要素说”,即增加具体制度这一要素。从制度的调整范围和功能角度,法律制度可分为宏观法律制度、中观法律制度和微观法律制度。宏观法律制度多指法律体系,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中观法律制度多指法律部门或部门法律,如民法、教育法等;微观法律制度,也称具体法律制度,是在法律原则的统领下,以法律概念和规则为基础,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制度,它是传统法律“三要素”的结晶,往往也是立法中重点问题的解决和亮点的凸现。如“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广东省工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综合对此制度作了规定,其内容包括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的申请主体、保障措施(基金垫支、依法追偿)和法律责任;其形式包含了概念(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等)、原则(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工伤保险工作应当坚持预防、救治、补偿和康复相结合的原则”)和规则(假定——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处理——先行支付和依法追偿;后果——承担相应行政处罚和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与标准,支付本应由基金支付的费用)。
法律概念是对社会有关现象和事实的共同特征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思维范畴。孙国华教授认为,按照涉及的法律事实要素的类别,法律概念可分为涉人概念(如公民、法人、行政机关等)、涉事概念(如所有权、违约、故意等)和涉物概念(如标的、证券、不动产等)三大类[4]。法律法规对重点概念或专业术语,一般会在有关条文中直接规定,如“行政强制措施”这一概念在行政强制法的第二条第二款中作了规定。但限于法律文本的篇幅,或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有些重要概念难于在单一法律法规中规定。对此,应在其释义中进行界定。对概念内涵的明确即实质定义,常采用种差加属方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编写的《〈广东省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保障条例〉释义》,对该条例第十九条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概念,在相应释义中作了定义——“珠江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和统一管理的要求,从区域整体上进行统筹规划,逐步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法律原则。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即是关于行政强制合法性原则的规定。
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逻辑规范一般由“假定、处理和后果”三部分构成。但从立法技术规范角度,在某一条文中不一定都规定三种要素,如“假定 ”可能隐含,“处理”和“后果”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条文中规定。前文所举“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对此已一并论述。
(四)把握地方性法规释义的重点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立法权限,地方性法规实际上可分为执行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和先行性法规。对于自主性法规和先行性法规,因其调整的属于地方事务或国家暂未规定的社会领域,其释义配套工作自应准确和周到。对于执行性法规的释义,因涉及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处理,亦即地方立法的立法体例选择问题,则应分类处理,突出重点。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委员孟庆钟所言,“立法体例一般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条例,对某一方面事项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范;一种是规定,对某一方面事项作部分的规定;一种是实施办法,对贯彻实施法律、行政法规作出比较具体的做法。”[5]因此,对于前述第二、三种情况,则应进行全面、准确释义。
对于前述第一种情况,上位法往往已作了详尽释义,则应重点对该条例针对上位法所作的细化和补充规定部分,以及紧扣地方实情所作的地方特色规定部分进行释义。具体法律制度的规定,是实现上述两个部分规定的重要途径。如《广东省工伤条例》规定的“工伤康复制度”,即是对上位法《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订)第一条关于“职业康复”规定的细化和补充(该条例仅在该条规定“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但未作具体规定)。
(五)建立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的常态化机制
首先,应明确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为一般工作原则。地方立法后一般应释义配套,但条文含义明确、修改较少的法规修正案等可例外。
其次,应明确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的主体及其职责。应以地方立法工作机构的名义组织撰写,以该机构的有关组成部门为承办部门和责任部门,并吸收政府法制和职能部门有关人员、专家学者参加,成立专责撰写小组,负责具体工作。
再者,应明确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的程序及时限。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的程序,不必与法律解释的法定程序相同,但亦应建立相应工作程序制度。程序上,地方性法规释义配套一般由组织分工、撰写、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审定和公布等环节组成。其中,应增强征求意见的针对性,将释义的全部或重点、存疑部分征求政府相关部门、涉及的公民和组织代表、包括法律专家和语言文字专家在内的有关专家学者等的意见;释义修改完善后,应由地方立法工作机构审定。时限上,一般应在立法后的3个月内完成所有工作。
最后,应明确地方性法规释义的名称和方式。一般应以地方立法工作机构或释义撰写小组的名义在当地地方立法pa视讯官网公布,释义名称宜统一为“某某法(指立法体例名称)释义”;事后视情况,可单独或会同其他部门,汇编成册或公开出版,其名称可酌情而定,但不应偏离“释义”这一核心题旨。
注释:
[1]【美】赫施著:《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版,第16~17页。
[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45~246页。
[3]【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204页。
[4]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75页。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2
在国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解释及其争议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有不同的解释规则,因此可能会发生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本文认为,合同解释作为合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问题,其法律适用规则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合同解释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其次适用合同准据法,特殊合同的解释则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则。
【关键词】合同解释 法律冲突 法律适用
严格履行合同既是当事人的义务,又是合同具有约束力的根本所在。但是,由于语言符号不是数学符号,它存在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缺陷,合同条款即使规定得再明确,也或多或少存在意思表示不明甚至缺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合同解释的争议;如果争议申请仲裁或诉诸法院,仲裁机构或法院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该争议的处理问题。因此,合同解释也就成为合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问题。合同解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释包括确定合同成立与否、确认合同的性质、发掘合同默示条款或暗含条款的含义,而狭义的合同解释只是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1]本文是从狭义上来论述的。
一、国际合同解释及其法律冲突
合同解释在国内合同与国际合同中的情形是不同的。对于国内合同而言,如果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发生争议,则可协商确定;如果不能协商确定而申请仲裁或诉诸法院,仲裁机构或法院就按照该国内合同法的有关解释规则确定。这里的争议发生在一国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涉外因素,因而不存在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也就不存在适用外国法的有关合同解释规则的问题。
对于国际合同而言,这种合同法律关系在合同的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三个因素中,至少有一个与外国发生联系。[2]如果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发生争议,争议发生后也未能协商确定,而有关国家的法律对该问题做了不同的规定,而且都主张对该合同法律关系行使管辖权,要求适用自己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因为不国家的合同法律可能包含不同的解释规则,而适用甲国法还是乙国法来解释合同,其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签订了一个借贷合同,其中有支付条款,单位用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借贷双方对支付条款中“元”的含义发生争议。依美国法,这个货币单位解释为美元,而依日本法,这个货币单位解释为日元。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即究竟适用何国法来确定该合同支付条款中“元”的含义。如果该合同是在法国订立的,则情况更为复杂。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有歧义的文字依合同订立地习惯解释,那么,该“元”的含义依合同订立地习惯,也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表面上是各国有关合同解释的规则不一致而发生的冲突,实质上是法律适用效力的冲突,即在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的条件下,内外国法律都竟相要求适用自己的合同解释规则来支配涉外合同的解释问题,因而产生的不同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释往往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大小。很显然,用美元还是用日元或其他国家的货币来偿还贷款或收回贷款,对借贷双方来说,其利益大小是不同的。因此,解决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便具有现实意义。
二、一般国际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
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就是按照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定的那个国家的实体法中有关合同解释的规则来确定合同条款的准确含义。笔者认为,合同解释作为合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问题,其法律适用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其独立性是指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有其自身的规则,其相对独立性是指合同解释作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没有自身规则可供调整的情况下,与合同问题的其它实质方面(如成立、效力、内容等)一样,一般受合同准据法支配。因此,合同解释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其次适用合同准据法。
(一)合同解释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
在合同法律适用理论上,一直存在“统一论”和“分割论”之分。[3] “统一论”主张合同所涉及的所有事项或争议均应受同一法律支配,因而合同准据法是唯一的。“分割论”主张合同所涉及的有关事项或争议应分别受不同法律支配,因而合同准据法是多个的。这两种主张各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立法、司法实践的支持,很难说孰优孰劣。正如有学者认为:“统一论”所强调的是合同内在要素的统一性,“分割论”所强调的是合同内在要素的相对独立性。[4]因此,在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笔者认为可以存在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因而应首先适用这种专门法律规则,但这种专门法律规则仍应服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它是经当事人选择而产生的。
解释合同就是探求当事人意欲赋予有关术语的真正含义,因而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是最恰当不过了。[5]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应适用某特定国家的法律于合同的解释,那当然应适用这一选择的法律,而不管合同准据法作何规定。例如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使用了一个含有甲国法律确定含义的术语,而该含义在该合同准据法中是晦涩难懂的,那唯一合理的就是认为当事人是想用甲国法来解释该术语的含义。又如在一个运输合同中,双方约定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适用英国法,那么一旦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对合同条款理解的争议,法院就必须适用英国法作出解释,即使该合同的准据法是美国法也应如此。法国学者巴迪福(h. batiffol)在认为,合同的解释应依自治的法律,因为这是当事人合意的主要结果,而且他还指出这是法国法院、英国判例、瑞士法院都采取的做法。[6]英国学者戚希尔(g. cheshire)和诺斯(p. north)也认为,合同的解释问题适用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的法律。[7]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3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程序法定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在近代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领主以及国王君主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或筹集战争费用的需要,巧立名目,肆意课税盘剥劳动人民。后来,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市民阶级抵抗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无代表则无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其萌芽初现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此后,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为了通过税收来筹集对付苏格兰军队的军费不得不两次召集议会,由于议会与之对立而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并将查理一世葬送在断头台上;直至“光荣革命”胜利的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又因“印花税”和“茶叶税”等激怒了其北美殖民地人民,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的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项)。[1](pp.25—26)
在法国,1788年巴黎的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法王路易十六为了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迫不得已在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就未曾开过的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路易十六也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就在这一年,法国了“人权宣言”,其中虽未直接规定征税问题,但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也就包括了征税问题。以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
西方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多注重在其宪法中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2](第58页)如日本,明治宪法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税率须依法律之规定”;《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又如意大利,其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还有埃及、科威特等国。
以上历史发展表明: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权力的依法律行使,故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3](第17页)
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故“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2](第58页)
二、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一)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达。”[3](第16页)
我们试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名词分解开来加以解释,以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理解:
1.“税收”概念之含义。笔者认为,税收是指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这一定义与税收的传统定义相比较,在形式上起码具有如下特征:(1)涵盖了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三方主体,即作为纳税主体之代名词的“人民”、作为实质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形式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4](2)突出了“人民”在整个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作用,与人民在反抗封建君主、争取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符的;(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由此淡化了传统理论中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使之更易为纳税人接受;(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意旨。
2.“法”概念之含义。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简单来说,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因此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所以,就“法”概念之含义而言,“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没有“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明白准确。
3.“定”概念之含义。对税收法定主义中之“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将“定”理解为“依据”,即国家整个税收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指导作用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第二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仅定位为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税收法定主义本身必须以法律(宪法)形式加以明文规定,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立法”之“立”,也就是说,在立法技术发达、立法形式多样的现代社会,“定”早已突破其最初作为“制定”的外延,而扩展到除此以外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等诸形式,换言之,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收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当然,就此而言,“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又没有“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全面准确。
4.“主义”概念之含义。如前所述,就“税收法定”之意,有称为“主义”者或“原则”者亦或“主义原则”者,故有必要加以辨析,以示其异同。所谓“主义”,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5](第1497、1408页)法的原则则是相对于法的规则而言的,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第56页)再来看英文“doctrine”和“principle”二词,虽前者主要作“主义”解、后者主要作“原则”解,但并非绝对,二者均可互译,视不同语境而定。由此来看,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或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或者直接将其称为“税收法定原则”并无很大不妥;假如说有区别的话,则“主义”的抽象层次和逻辑顺序要高于“原则”,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而将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或税收司法等的基本原则。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7](第50—54页)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2](第59—60页)又有的认为包括“税种法定、要素明确、严格征纳和程序法定”等内容;[3](第16页)还有的则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作多项分解列举。[8](第152页;第4—5页;第156—157页)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如下三个部分:
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7](第50页)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
笔者认为,所谓税收要素,是指所有税种之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全面展开所需共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税收要素既经法律规定,则为税法要素,是各单行税种法律共同具有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税法要素之含义,进而确定税收(法)要素的具体内容:(1)税法要素主要是针对税收实体法、亦即各单行税种法律而言的,但并不排除其中的程序性规定,如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等;(2)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税种法律都同时具备的,具有一定共性,仅为某一或某些税种法律所单独具有而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内容,不构成税法要素,如扣缴义务人等;(3)虽然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单行税种法律都必须具备的,但并非要求在每一部税种法律的条文中都必须对诸税法要素一一予以明确规定,有时可以通过其他非税种法律的形式对某一税法要素作出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五章就对违反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因此,尽管某些税法要素没有在单行税种法律中得以体现,但却规定在其他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税收程序性法律中,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税种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税收实体法律的内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法要素具体包括:税种,[9]征税主体,[10]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
税收要素须以法律定之,这一点无须多言。关键是,法律如何对税收要素加以明确且无歧义的规定。因为,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对于那些立法技术尚不发达,习惯于以原则性语言进行立法的国家,如我国,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3.程序法定原则。前两个原则都侧重于实体方面,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11](第84页)在税收法制建设中也有类似情况,要么在立法时不注重对程序问题作出规定,要么是有一些规定却又不依照执行,结果是由于程序缺失或不当,致使实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未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1](第86页)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2)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为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3)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以上三部分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完整内容。
三、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在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介绍到我国来的。[12](第150—153页)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目前,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已呈现出取代我国传统税法理论中的税法基本原则,而被直接确立为我国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趋势。[13](第31—32页)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一规定隐含了或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3](第18页)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的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但立法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使得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法律中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2](第59页)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修改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要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不论是税收法制还是税收法治,都没有充分执行或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甚至表现出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比如,单行税种法多为税收行政法规形式,降低了税法的整体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税收环境的培育。无论如何,作为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当然应作用于税收法制建设的全过程,而体现在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如此才能真正达到税收法治之状态。[14]
「注释
[1] “税收议案必须首先在议会提出。税法应当在立法机关的下院提出,这一传统来自英国。在那里,由于人民直接选举下院成员,而不选举产生上院-贵族院,故下院更倾向于反映人民的意愿。在美国,这一规则却有所不同,因为人民既选举产生众议院,又选举产生参议院。此外,参议院得以修正税收议案,甚至可以达到将其完全改写的程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dapted from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world book, inc., 1986.
[2]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3] 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j].税法研究。1997(1)。
[4] 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j].法学研究。1999(4)。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7](日)金子宏。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8] 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罗玉珍主编。税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9] 传统税法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
[10] 传统税法理论中课税要素虽含税法主体,但仅指纳税主体。此为其一大缺漏。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税法要素之外呢?且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
[11]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12] 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原则;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4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进行交往最重要的形式是合同,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合同纠纷。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来约定权利义务,同时,当事人的约定也是法官裁判合同纠纷所依据的最重要的事实。对于合同事实的认定正确与否直接决定案理处理的正确性。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是不是清楚明白,不需要任何解释呢?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由于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多义性和歧义性,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所限及法律知识欠缺,也往往造成合同中的用词不当,使双方真实意思难以明确表达。另外某些当事人故意使用不适当语言文字,以达到其不正当目的。因此,法官在裁判合同纠纷过程中,需要对合同进行解释,以正确认定事实,明确裁判逻辑思维中的小前提,得出正确的裁判结果。笔者发现,部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大前提即法律规定的解释比较重视,但对小前提即决定案件事实的合[1]同条款的解释重视不够,以致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当做法。笔者认为,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对法官裁判来说同等重要。法官在裁判合同纠纷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合同解释理念与掌握正确的解释方法。
一、合同解释的含义
解释,又称诠释,含有分析、阐明、说明、注解之意。合同解释是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从而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活动 [2].就合同解释主体来分,合同解释有当事人解释和法官解释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是法官解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难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解释合同条款,而法官为裁判需要亦需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但是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是权威解释,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解释对法官解释有参考作用,但是没有约束力。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可以成为合同条款的广告、要约、宣传注明:某某享有最终解释权。这样的说明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事实上,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只能属于法院。
合同解释目的是通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以探寻当事人的真意,从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合同解释过程也是一个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过程。但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合同解释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真意呢?对于单方意思表示,我们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意。但是,订立合同是双方甚至多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而且可能他们的“真意”存在差别;如果以一方的真意为标准,那么还存在对另一方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此,在合同解释的标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主观主义坚持把探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意思放在首位。客观主义则拒绝这样做,而是以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所用语言文字的含义为标准,即所谓合理的客观标准[3].我们不妨先看看部分国家或地区立法采取的合同解释标准。《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解释时,应探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文词”,第157条则规定:“解释合同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5]《法国民法典》所采用的是主观主义,把探求当事人意愿放在第一位,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德国民法典》第133条采用的也是主观主义,但是第157条进行了修正,还应按诚实信用及交易习惯进行解释,即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的解释不再限于探求当事人究竟如何思想,而是以某种客观标准(诚实信用与交易习惯)去认定当事人应该如何考虑,意味着对当事人的意志进行了适当限制,加强了对交易安全及交易秩序的保护,采用的折衷立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条实际是由《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而来,但是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进行合同解释,因而实务上采用的也是折衷立场[6].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此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合同法》采用的是折衷标准。但是二个标准并非并列,同等重要。笔者认为,合同解释应首先探寻当事人的真意,在不能求得当事人真意,或依据一般解释方法明显不公平、不符合常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方法解释确定合同的含义。不能够在当事人意图已明确的情况下,以客观标准来曲解当事人的意思,那样会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
二、合同解释的方法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下列内容进行确定:合同的性质、合同条款的准确含义、合同漏洞填补等。确定以上内容都属于合同解释的事情。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才能达到确定合同含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目的。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方法的规定有以下几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是对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六十一、二条是规定在当事人没有明确规定时,如何确定合同的内容,即合同漏洞的填补;第一百二十五条是合同解释规则的一般性规定,即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上述规定来看,立法者对合同的解释是高度重视的,规定了较详细、全面的合同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正确运用上述方法去解释合同,裁判案件。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5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1
第一章 刑法适用解释之存在 3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的动因 3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之论证 7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的范围 11
第二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 15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 15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特点 18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 20
第三章 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之制度化 22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制度化的思想基础 22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制度化的实践分析 25
第四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 30
第一节 正式的法律文件 31
第二节 非正式的法律资料 32
第三节 法学理论知识与一般社会观念 33
第五章 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 35
第一节 主观解释思想 35
第二节 客观解释思想 36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 37
第六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 40
第一节 刑法解释方法概述 40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方法 41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方法的运用 43
第七章 刑法适用解释创造性的限度 48
第一节 扩张解释、类推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概念 48
第二节 类推解释之禁止 49
第三节 扩张解释之界限 50
注释 53
参考文献 57
后记 62
中 文 摘 要
刑法适用解释是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最初由储槐植教授在《刑事一体化与刑法关系论》中提出,但是,刑法学界对此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借鉴西方法解释学的某些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刑法学理论和我国的法制实践,对刑法适用解释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文章的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做了说明,主体部分共八章。
第一章论证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刑规范的适用解释是客观存在的。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的原因在于,刑法规范相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的特点。刑法规范的这些局限性是由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和法律语言的局限性决定的。
刑法适用解释客观地存在于刑法适用过程中。刑法学者往往认为刑法适用的过程是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理。大前提是刑法规范,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范,结论是判决结果。笔者通过对三段论逻辑推理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笔者提出并论证了刑法适用解释的过程是:1、找法,找出将要适用的刑法规范。2、解释,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3、归摄,判断案件事实是否能归摄于刑法规范之中。4、判决。因而,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对刑法的适用解释是存在的。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于所有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但是明显地表现在疑难案件审理过程中。
第二章对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特点及其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进行了研究。
什么是刑法“解释”?刑法学者往往认为“解释”就是解释活动形成的书面结论,刑法解释是最高立法、司法机关对刑法典所作的一般规范性解释文件。但是,刑法适用解释之所谓“解释”不是书面解释结论,而是法官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过程中对刑法规范含义、内容的理解,即现代解释学之所谓“理解就是解释”。从思维活动的角度来说,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是作出刑事判决的法官及合议庭及其他影响判决作出的主体,在目前“法院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构造下,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往往呈现“无面目性”的特点。刑法适用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而不是刑法条文,规范是条文的内容而条文是规范的形式。刑法适用解释的思维过程和结论的载体是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说理是法官表明刑法适用解释过程正当性、合理性的过程,也是外界对刑法适用解释进行监督的依据。
刑法适用解释具有个案关联性特点,刑法规范作为刑法规范往往逻辑自足,但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时往往显得抽象概括模糊;刑法适用解释在具体案件审判中发生,解释结论只具有个案适用的效力。刑法适用解释还有主观性特点,表现在它不仅需要通过法官运用个人主观经验理解规范,而且往往还需要法官作出价值判断。
刑法司法解释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刑法适用解释是一种法律适用思维活动,刑法司法解释有时也还需要进一步在审判中由法官进行适用解释。
第三章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权力的制度化的相关问题。
要将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制度化,首先要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是承认法官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是否违反了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的原则。本文的研究表明,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是相对的,法官在一般规则留下的空间内享有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是法律运行的规律,它不违法立法权、司法权分立的原则。其次是承认法官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是否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本文的研究表明,现代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承认法官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不相矛盾。
对于法官的法律适用解释权力,有的国家在宪法中明文加以规定。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法官的法律适用解释权力,本文认为:对此应该理解为,宪法在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时,就已经授予了法官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因为刑法适用解释权是审判权力中的内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刑法、刑法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明确的地方,法官就面临着进行创造性适用解释的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各级法院是应该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司法解释呢,还是应该自己进行创造性适用解释,并没有统一的制度规定。本文认为,对于实践中普遍发生的案件,如果需要进行创造性适用解释,各级法院应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利于法制统一;对于实践中发生得较少的非普遍性案件,各级法院可以谨慎地作出创造性的刑法适用解释。
第四章对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进行了研究。 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是指对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具有意义的法律文件、资料、材料和其他因素。也就是,当法官在对特定的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他应该考虑那些方面的因素。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包括正式的法律文件、非正式的法律资料、法学理论知识和一般社会观念等。
正式的法律文件包括刑法、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行政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法规。特定的刑法规范及其法律概念往往只有在上下文整体中才能确定其含义,对特定法律规范的解释必须关注其上下文,以确定正确的含义。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文件是特定机关对刑法作出的有权解释,法律适用者在理解和解释刑法规范时必须遵循。大量的刑法规范(主要是行政刑法规范)规定行为构成犯罪以违反相应行政法律法规并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条件,因而对这些刑法规范进行适用解释是还需要参照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此外,一些刑法规范含义的确定需要参考行政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规定
非正式的法律资料主要是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和其他政策。我国刑法立法强调对党和国家基本政策和刑事政策的体现,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适用解释的时候,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从党和国家的政策出发,去揭示刑法规定的含义。党和国家政策作为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的根据,表现在:有些刑法规定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阐明其含义;有的刑法规定需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进行或者限制或者扩展解释。
法学理论知识对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正确的解释刑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刑法解释学理论,它主要就是研究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解释现行刑法规范的,因而对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此外,一般社会观念,如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经验常识、道德善恶观念等,在刑法适用解释中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刑法解释基本思想对主观解释思想和客观解释思想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并以此为根据提出刑法适用解释应遵循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下章中研究刑法适用解释方法的基础。
主观解释思想立足于法律的自由保障价值,认为法律解释应该探求法律文本内的或者文本外的立法原意;客观解释思想则立足于法律的社会保障价值,认为立法原意是不存在和不可知的,法律解释应该根据社会变化作出合目的性的解释。客观解释之所谓“客观”,是指客观现实。
刑法的自由保障价值与社会保护价值不可偏废,但从刑罚手段的严厉性和效益有限性出发,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应该具有优先于社会保障机能的价值。应该认为,立法原意是可以探知的。所谓的“立法原意”可探知,并不是不是说立法时各位立法参与者头脑中抽象的思想和情绪是可探求的,而是说立法者借助于文字符号这种载体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是可以通过分析立法相关资料、立法前后社会环境和重大事件等而探知的。任何法律规定都具有立法者所赋予的原本意义,立法原意对于立法者来说是主观的但对于解释者来说则是客观和可探知的。
基于以上分析,刑法解释应采折衷的立场。具体而言,刑法解释应以主观解释思想为基础,如果依主观解释思想得出的解释结论与一般之合理观念严重违背,则应采取客观解释思想立场。
结合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实际情况考察,我国的刑法立法、司法解释应该采主观解释思想为基础的前提下,大胆的采取客观解释思想的立场。这是因为它们由于是一般规范性解释,对各级法院有普遍适用效力,依客观解释立场进行解释不会造成法制不统一。且解释程序、解释者素质较好,因而解释质量较高;有学者认为大量采取客观解释立场会侵犯立法权,但是以一种模糊的未经实践验证的抽象观念来否定司法实践实现公正的价值,何其迂腐!各级法院的刑法适用解释,应在采主观解释思想为基础的前提下,谨慎地采用客观解释思想的立场。各级法院对于实践中普遍发生的案件,如果依主观解释立场得出的解释结论严重不合理,应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以保证各个法院的司法统一,对于非普遍发生的案件,亦可谨慎地依客观解释立场作出判决,并应该说明判决理由。 第六章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从法律解释方法概述、刑法适用解释方法、刑法适用解释方法的运用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法律学者对法律解释方法作了较全面地列举和说明,主要有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系统解释、扩张解释、缩限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这些解释方法的视角标准各不相同,其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刑法解释方法应该只有文义解释方法、法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其他解释方法或者是大致落入这几种方法的范畴之内,或者只是作为辅助性的方法而不具有独立的实用价值。
因而,具有独立意义的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是文义解释方法、法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方法和法意解释方法源自主观解释思想。认为只应从正式的法律文本自身探求立法原意的主观解释思想产生了文义解释方法;而认为还应该从非正式的法律文件、法律资料和对立法社会环境等的考究中探求立法原意的思想产生了法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源自客观解释理论,是根据客观社会实际,基于对法律的社会目的的考虑而解释的方法。
平义解释方法应是我国各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当中的首要的刑法适用解释方法。大量的常规案件通过平义解释方法就能得出唯一合理的解释结论。即使运用平义解释方法没有得出唯一合理的解释结论,所得出的诸种可能的解释结论也为法意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了选择的基础。平义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普通含义解释方法和专门含义解释方法。运用普通含义解释方法,首先要找出语词或词组的字面含义,然后运用系统解释方法确定其在上下文中的恰当意义。法律术语的专门含义可以由受过法律专门训练者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它在法律中使用的历史来确定。
当运用平义解释方法得出的解释结论仍然不确定时,应运用法意解释方法进行解释。法律用语的立法原意应该在平义解释方法提供的选择范围内,通过分析立法相关资料、考察立法背景等方式确定。
当运用平义解释方法或法意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明显的不符合常理时候,应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以获得合理的结论。目的解释方法运用的关键是通过实践理性挖掘法律内在的价值取向,它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各级地方法院尚不完全具备运用目的解释发方法的实践基础,各级法院在应谨慎的进行目的论解释。当需要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进行解释的案件的发生具有普遍性时,各级人民法院应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司法解释。
第七章刑法适用解释的创造性的限度从扩张解释、类推解释、类推适用的概念,类推解释的禁止,扩张解释的限度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般认为,扩张解释是在法律用语的立法原义之外而在其所可能包含的最大意义范围内的解释,类推解释是超出法律用语可能包含的最大意义范围之外的解释。但是,亦有人认为扩张解释是超越了法律条文在语言学上的意义范围的解释,由此产生了禁止扩张解释的立场。还有认为在扩张解释范围内承认类推解释的观点,据此有类推允许说。这些观点只有概念运用上的区别,并无本质的差异。我国学者一般将类推解释与类推适用相区别,但从思维过程看,两者并没有区别,“适用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类推适用)应该理解为就是对该“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进行超出起其可能意义范围的解释(类推解释)。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容之一就是“禁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不是根据正当程序的法的创造,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违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和,混淆了法与道德的区别,丧失个人利益的保障,易招致国家权力的肆意行使和对国民自由的不当压制,与法治国家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为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所不允许。但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上则具有一致的价值立场。
关于扩张解释的合理限度,应求诸于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划分的基准应该是:一般人会认为“如果那个行为按照这项条文加以处罚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按照同样的条文加以处罚是理所当然的”。具体的判断方法是:首先确立该待解释的法律词语概念的一般观念形象,其次理解该待解释法律词语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再次判断如果将该法律词语解释为涵括待决法律事实要素,是否与该法律词语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相一致。
关键词:刑法 适用解释
论刑法适用解释
绪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什么是刑法解释?刑法解释是对现行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含义进行阐释的活动及其结论。刑法学者一般认为,刑法解释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学理解释。那么,法官在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呢?对此,刑法学者一般持否定的态度。亦有少数学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现行刑法所作的一般规范性解释,而且包括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对刑法规范的解释 。北京大学的储槐植教授认为,在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之外,还存在刑法适用解释,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刑法所作的个案性解释 。
以上争论的焦点在于:首先、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着法官对刑法的解释,其次、如果存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解释,它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有什么不同?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是否存在,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在第一章中进行详细论证。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及其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笔者在第二章中进行了分析论述。
第三章对刑法适用解释权力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法官在审判中对刑法的适用解释是实际存在的,但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中对法官是否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并没有明确规定。此外,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应该保持在多大范围内,即:在审判中需要进行创造性解释时,那些应该报请司法解释,那些应由法院及法官进行适用解释,亦没有法律规定。本章中,笔者结合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
法官应该怎样进行刑法适用解释的操作呢?对此,理论上缺乏研究,实践中法官往往仅凭经验行事。基于此,笔者在第四、五、六、七章对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操作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指导。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刑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本文澄清了刑法学理论界对于刑法适用思维过程的误解,提出并证明了法官对刑法规范的适用解释是实际存在的,并且是合理的。这一研究结论对于刑法学理论中的一些基础性理论研究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二、对刑法司法制度建设的意义。
但法律制度上对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权力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又实际存在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由此引起认识上的混乱。此外,在刑法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司法解释仍然没有解释明确的地方,法官面临着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的难题,由于抽象规则与具体案件的差距,这种情况大量存在,法官怎么办?是所有的这类疑难案件都应报请司法解释呢,还是法院及法官应该完全自己进行适用解释?制度上也没有统一。本文针对实践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三、对于司法实践的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司法实践。法官要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首先必须理解和解释刑法规范的含义。如何进行理解和解释呢?理论上缺乏研究,实践中,法官往往在简单案件中凭经验行事,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的疑难案件中就感到无所适从。本文对刑法适用解释的操作进行了研究,对刑法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章 刑法适用解释之存在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之动因
法官之所以存在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是由刑法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刑法规范的局限,表现为刑法规范的抽象性、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刑法规范的这些局限性,决定了它与具体案件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它给刑法适用者留下了解释的空间。
刑法规范存在的局限性,有些是由立法者认识的局限决定的,有些是由法律语言的局限性决定的。
一、刑法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
(一)共时性认识局限
共时性认识局限,是指立法者在立法时,对当时社会中的各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认识是有限的。任何刑法立法都是立法者在总结自己过去同犯罪作斗争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其他立法者的经验的基础上所制定的。但是,刑法立法者的生活经验总是有限的,他所能认识的其他立法者的经验也是有限的。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地方大,人口多,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犯罪行为千差万别,同一种犯罪行为又存在着各种社会危害性不同的犯罪样态。因而,刑法立法者不可能全部认识社会生活中所有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刑法立法者的这种认识局限性,表现在刑法中,就是:1、犯罪构成规定只对典型的案件具有针对性,难以明确含括非典型案件。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这一刑法规范是立法者从常见的杀人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对于一些非常见的行为,则仅仅根据该条难以明确判断出立法者是否意图包含它们。例如,某甲知道某乙有心脏病,生气时有生命危险,为谋害某乙,故意在某乙面前指桑骂槐,导致某乙心脏病发作死亡。这种行为,很难判断立法者是否意图包含在百刑法232条中。2、犯罪构成要件对行为样态的描述往往不完整,使法律适用者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里,“因逃逸致人死亡”中,肇事人“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仅仅指过失,还是包括间接故意?立法者并没有描述出来。
(二)历时性认识局限
所谓历时性认识局限,是指刑法立法者在立法时对立法之后社会中的各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认识是有限的。刑法立法者的立法内容总是对立法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行为的认识,即使立法者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也是极为有限的。但是,社会生活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立法当时的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变得仅仅具有较小或者没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一些立法当时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变得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另外,有些事物在立法的时候可能根本不存在,而是在立法后才产生的,立法者更是难以预见。
刑法立法者的这种历时性认识局限,表现在刑法中为:1、立法者往往在刑法条文中留下一些空缺结构,使条文具有概括性,以便能包含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情况。如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其中,“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就是一种空缺结构。2、有些新的行为的确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立法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例如,法国刑法典制定得很早,当时电力根本就没有应用于日常生活,因而按立法者的意思,法国刑法中的盗窃罪中之所谓“财物”应该认为根本不包括电力,但是被告人私自从屋外电线上引入电线,偷用电力,是否构成盗窃罪呢?立法者没有给法官答案。
二、法律语言的局限性
刑法规范是通过刑法条文表现出来的,刑法条文是由法律语言表达出来的。作为刑法载体的语言本身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一)法律语言是有限的
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同样,法律语言也是有限的。但是,社会生活确实多姿多彩,无限多样的。用尽人类所有的语言,也无法把社会中的各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都准确、具体、详细的描述出来。正如学者所说:语言是无限客体之上的有限的符号世界,世界上的事物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要多得多 。例如,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意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该条中仅有了“着手”二字来描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无限多的具体的犯罪行为的“着手”的形态,既包括盗窃的“着手”,也包括杀人的“着手”等等;仅其中杀人的“着手”中,就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具体的样态,例如,投毒杀人的着手,放火杀人的着手,等等;而这当中仅投毒杀人的着手,又包括各种不同方式的投毒杀人的“着手”。可见,由于法律语言有限,而社会生活无限,因而法律语言无法把所有不同的社会危害行为正确、具体、详细的描述出来。
(二)法律语言是多义的
语言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所要表达的对象确是无限多的,每一个字、词都兼顾着表达多种对象的任务,因而,语言就必然是多义的。
法律语言的多义性,有时可以通过分析上下文语境来消除。例如: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强奸妇女的,处……”,“妇女”一词,在汉语中既可指已经结婚的女性,也可泛指所有的女性,但根据语境分析,可知在该条中指所有女性。
但是,分析上下文语境只能使法律语言的含义变得相对明确一些,却无法使它绝对的明确。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这里的“人”,是否包括头部已经母体,但尚未完全脱离母体的胎儿?是否包括心脏、脉搏已经停止跳动、呼吸已经停止但是脑电波尚未停止的人?从法律上下文语境中,无法得知。
(三)法律语言具有模糊性
语言具有模糊性,法律语言也具有模糊性。英国法学家哈特说:“任何语言,包括法律语言,都是不精确的表意工具,都具有一种“空缺结构”(open texture),每一个字、词组和命题在其‘核心范围’内具有明确无疑的意思,但是随着核心向边缘的扩展,语言会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在一些‘边缘地带’,语言则是根本不确定的,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不存在绝对或唯一的正确答案,解释者或者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需要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中和推理结论中作出选择,甚至可以扮演创建新规范的角色 ”。
哈特的上述论述是相当精辟的,语言的含义的具有天然的模糊性,法律语言亦然。例如,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法律用语的含义都有着模糊性的“边缘含义”。择其中典型的“暴力”、“胁迫”两个基本点概念分析如下:
“暴力”:试分析下列夺取他人财物过程中发生的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为。(1)被告人一拳把被害人打翻在地,致其不能动弹,然后夺走了被害人的财物(2)被告人将被害人往后一推,被告人拌在石头上,摔倒了,被告人乘机夺走了被害人的财物(3)被告人与被害人迎面而过,被告人有力的背膀将被害人碰了以下,致使被害人险些跌到,被告人乘机夺走了被害人的财物。在上面三种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为中,第一种是典型的暴力行为,处于暴力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范围内,第二种和第三种就逐渐一步步远离“暴力”概念的“核心意义”,第三种行为完全是在它的边缘意义范围内。刑法263条之“暴力”概念是否包括第二、三种行为,并不明确。
“胁迫”:试分析下列在夺取他人财物过程中发生的带有“胁迫”性质的行为。(1)被告人手持匕首对被害人说:要钱还是要命?(2)被告人叫被害人停下,然后被告人一拳将路边的大树击倒,然后对被害人说:拿点钱来用一用。(3)被告人叫被害人停下,挡在被害人面前,不让被害人通过小巷,对被害人说:留下买路钱。但被害人亦可以转身离开。在以上三种行为中,第一种处于“胁迫”概念的核心含义中,第二、三种则逐渐远离其核心含义,它是否包含于刑法第232条之“胁迫”概念中,是不明确的。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之论证
“解释”一词在有两种意义,一是作名词用,意思是对某文本进行阐释后形成的书面或口头结论;二是作动词用,是指对人们理解文本的含义并将其理解表达出来的过程。法官对刑法的适用解释主要是从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解释”一词的。在这里,解释是指理解者对法律规范的含义的理解。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于刑法适用过程中,因而,刑法适用解释是否存在,应该通过研究刑法适用的思维过程来找到答案。
一、刑法适用的思维过程
要证明刑法适用解释之存在,首先要了解刑法适用的思维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毫无疑问,刑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着对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这是因为,刑事判决的正当性在伦理意义上和法制意义上都依赖于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1、从伦理角度看,三段论推理能产生一种“逻辑强制力” ,有力的证明了对罪犯判处刑罚的正当性。所谓“逻辑强制力”,是指一方试图从逻辑上强迫另一方承认已许下的诺言并履行。人是理性的动物,个人的承诺应该遵守,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也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信念。刑法事先公布,为公民知晓,其性质政府和大众之间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持续存在而建立的有关“自由”的社会契约。契约的本质是承诺,因而遵守刑法规范的要求就是遵守个人已经作出的承诺。刑法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相联系,犯罪是违反了刑法,从而违反了个人向社会所作的承诺,因而必须承担否定性的后果——刑罚,以至可以认为是犯罪行为自身产生了刑法规范的运用。因此,惩罚是三段论逻辑推理产生的逻辑强制力的必然结论,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对犯罪者判处刑罚是正当的。2、从法制角度看,三段论逻辑推理表明:法官是根据刑法立法者的意志进行裁判,刑事判决的结果是隐藏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刑事判决的是执行民选的代表所制订的刑法规范的结果,判决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法官个人的
意志的体现。这在民主政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无疑是对刑事判决正当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那么,在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过程中,是否存在对刑法的适用解释呢?
按照概念法学的理解,法适用过程表现为通过三段论法的逻辑推论获得判决的过程。法官严格按照三段论法作逻辑推理,遇有法律条文意义不明,只能探究立法者明示的或推知的意思。法律以外的因素如经济、政治、伦理等的考虑,均属于“邪念”,应一概予以排除,法官是执行法律的机械,判决之获得犹如文件之复印 。就刑法而言,刑事古典学派就是这种简单三段论的推崇者。贝卡利亚说: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一旦法官被迫或自愿做那怕是两种三段论的推理的话,就会出现捉摸不定的前景 。
依照这种思路,刑法适用解释的过程为:1、找法,找出将要适用的刑法规范。2、归摄,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可以归摄到刑法规范之中。3、判决。
例如:1998年某日赵某(女)向广西南宁市东新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其丈夫李某(男)离婚,东新区法院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1998年6月4日,赵某回到李某住处收拾衣物时,李某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赵某发生了性关系。后东新区检察院以强奸罪对李某提起公诉,东新区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判决李某无罪。
找法: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该案件的法律适用的思维过程,按照概念法学的观点应该是:
归摄:李某的行为不是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
判决:李某的行为不符合刑法236条之罪状规定,因此李某无罪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思维过程,判决结论是从作为大前提的刑法第236条中推导出来的,是立法者的意志的体现,法官只是在执行立法者的意志而已。法官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参与,因为三段论逻辑推理是不需要推理者个人意志的参与的,“任何一个能够将两点连接起来的人都可以作出这种推理 ”。
然而,稍加思索就可以看出,上述关于刑法适用过程的简单三段论的思维过程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我们把自己放到法官的位置稍加体会,就会发现法官并不是象概念法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机械的立法意志的执行者,法官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其次、我们也会在思索,假如李某和赵某不是夫妻关系,强奸罪肯定会成立。为什么李某与赵某是夫妻关系,强奸罪就不成立呢?刑法第236条并没有对夫妻与非夫妻的情况加以区分,那么法官是如何从236条中得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的结论的呢?
实际上,概念法学者关于刑法适用思维过程的论述的谬误在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刑法适用解释。笔者认为,刑法适用的思维过程包括:1、找法,找出将要适用的刑法规范。2、解释,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3、归摄,判断案件事实是否能归摄于刑法规范之中。4、判决。
找法: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述案例的刑法适用思维过程是:
解释:刑法第236条规定中的“强奸”概念,不包括丈夫在婚姻存续期内,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归摄:李某的行为不是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
判决:李某的行为不符合刑法236条之罪状规定,因此李某无罪。
二、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之论证
三段论推理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识别出一个大前提(例如,所有的人都会死)第二步是你应该用大前提表述一个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第三部是得出结论(苏格拉底会死)。大前提是一项一般规则,它描述包括许多成员的一群人的情况,因而也就允许一种将该规则制定个体置于群体的结论。例如上例中推理的有效性在于,“苏格拉底会死,是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中‘人’的定义之中了,第一个前提实际说的只是,这里有一个贴了标签的‘人’的箱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会‘死’,第二个前提告诉我们这个像子里的东西都有个名字牌,其中有一个写的是‘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箱子时,我们知道他会死 ”。
可见,三段论推理基本方法是:如果某个体本来就是某群体中的一员,如果该群体适用某一结论,则该个体适用该结论。三段论逻辑推理并不具有创设任何新知识的功能,推理本身对于推理的有效性(即结论的必然性)是没有问题的。就法律推理而言,推理的有效性的关键是:一、识别一个权威的大前提,二、明确表述一个小前提,三、推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而就成文法的推理而言,大前提本来就是权威的,不需识别。只要能用大前提的语言表述一个小前提,则结论必然是有效的。然而能否用大前提的语言明确表述一个小前提恰恰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规则并不能确定它们的适用范围,一个案件的事实并非事先就包装在规则的语言中,规则甚至不能包含其自身的适用标准 ,例如,刑法第249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但是,怎样的行为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该条并没有明确,须待法官的判断。因此,在任何案件中,法官肯定都需要首先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解释,确定其内涵、外延(适用范围),然后才能判断出刑法规范是否能够包摄具体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
以上关于三段论逻辑推理的研究表明,由于刑法规范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模糊性的特点,因而不经过解释,它就不可能成为三段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法官要将刑法规范适用与具体案件,必须首先结合具体案件对刑法规范进行适用解释。刑法适用解释是必然存在的。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存在的范围
一、刑事自由裁量权范围研究评述
我国刑法理论上由于尚没有对于刑法适用解释展开研究,但是在关于刑事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
关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在现行刑法规定幅度内的量刑权,即,对刑法量刑规定不确定性的斟酌处理权。有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在坚持罪刑法定、有法必依的原则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的犯罪分子,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视情选择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个人特点相适应的处罚方法 ”。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刑法授权审判员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斟酌案情裁量刑罚的权力 。”另有学者干脆只提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认为“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相对法定刑的体制下,根据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按照刑法的规定,在法定刑幅度之内,对犯罪分子自由裁量刑罚的权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止刑罚的自由裁量,还包括犯罪的自由裁量,这种对犯罪的自由裁量权包括:(1)在罪与非罪的临界状态,决定案件性质的自由裁量。一是某些临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司法人员和律师认识分歧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决定,二是刑法对某些构成犯罪情节、后果规定极为原则笼统,此类临界行为之性质则由法官裁量决定 。(2)为适应刑事案件复杂多样的需要,我国刑法有一些扩大法条适用性的“其他”,这些“其他”规
定,包容了有关法条列举不全的一些具体情形,若遇到此类情况,法官可依据立法精神行使自由裁量权:直接引用该法条作合符原义又大于其自面含义的扩大解释,灵活适用该法条 。
上述第一种观点否认法官存在定罪的定罪自由裁量权,是概念法学思想的反映,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观点承认法官存在某些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第二种观点脱离具体的案件谈法官对刑法中的那些法律规范及法律用语享有自由裁量权,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例如: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侮辱”这一概念为例分析:1、某甲(胁迫)被害人吞吃粪便。2、某乙(胁迫)被害人作出笑容状。3、某丙(胁迫)被害人骂自己是笨蛋。
刑法第237条之“侮辱”概念如何理解,是否包括甲、乙、丙三种行为?某甲的行为是典型的侮辱行为,法官在判断是几乎不享有自由裁量权。某乙、某丙的行为虽然带有侮辱的性质,但是并不是典型的侮辱行为,因而法官在判断时,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法律用语同“侮辱”这一概念一样,在遇到典型案件时,法官没有或者只有较小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遇到非典型案件时,法官则享有较大的自由财量的空间。因而不结合具体情况,笼统的说法官对刑法中的那些法律用语享有自由裁量权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二、刑法适用解释存在的范围
(一)刑法适用解释存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的审判中。
在任何案件的审判中,法官要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都必须要首先理解刑法规范的含义。而理解刑法规范的含义,就是对刑法规范的解释。
语言文本的含义并不是明确而具体的,相反,它存在着模糊的“边缘意义”范围。在语言的“边缘意义”地带,它究竟包括那些内容,不包括那些内容,并不是明确而具体的。理解者必须根据个人的知识、经验、价值倾向等作出判断和取舍,这就是对语言意义的解释。
例如,法官在遇到婚内强奸的案件时,要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首先要理解该刑法规范的内容。但是236条中的“强奸”,是否包括婚内强奸呢?法官可能认为为包括,也可能认为不包括。这种理解就是他对“强奸”概念作出的解释。
刑法适用解释虽然存在于所有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但是在典型的、常见的案件中,刑法适用解释的存在是潜在的、不明显的。例如,张某为了抢劫钱财而用匕首将他人杀死。在一般人看来,刑法第232条的“杀人”概念中显然是包含张某的此种行为的。法官将“杀人”这一概念理解为包含张某的此种行为,似乎是必然的,不存在法官的主观性判断。但是,实际上,法官对“杀人”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即“杀人”是否包括“为抢劫钱财而用匕首将他人刺死”的行为)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法官这时候的主观性判断是潜在的、不明显的。本例中法官的主观性判断是一种经验判断的过程,而不是象上例(“强奸”是否包括婚内强奸)的判断那样是一种价值判断性过程。这种经验性判断不是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肯定是存在的。试想,如果一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关于杀人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知识、经验,他能够很轻易的作出“杀人是否包括‘为抢劫钱财而用匕首将人刺死’”的判断吗?肯定不能,法官的经验判断是肯定存在的。可见,即使在普通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也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得不明显而已。
(二)刑法适用解释明显的表现在疑难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刑事疑难案件指非典型、非常见的刑事案件。疑难案件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刑法规范是否能够包摄具体的案件事实,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对此作出“是”或者“否”的答案,似乎都有其道理,通常来说,只能通过选择,不能通过断定决定取舍。其二、这种案件的判决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 。
刑事疑难案件包括两种:一、从刑法规则的语言看,有些案件因规则术语或概念显得模糊不清而难以处理,这类案件属于语言解释的刑事案件。例如,作为盗窃对象之“财物”是否包括电力?杀人罪之“人”是否未出生的胎儿?二、从规则适用的结果看,某些案件如果直接严格适用刑法规则会导致某些明显不公正不合理的结果,这类案件属于处理结果有争议的疑难案件。例如,被告人盗窃他人的一条价值100万元的名贵的狗,被告人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只把它当作一般的狗杀掉并卖掉狗肉,获得赃款50元。那么,是否应该依狗的市场价值100万元计算被告人所偷盗的财物的价值,并判处被告人死刑?如果这样判决,是否过于严厉?
刑事疑难案件的这些特点,使一般人对于刑法规范的含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法官必须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条件下对它作出解释。这样,在刑事疑难案件的审判中,法官对刑法的理解的主观立场就明显的表现出来,刑法适用解释的存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
我国以前的刑法学研究中,一般认为刑法解释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学理解释,对于刑法适用解释几乎没有研究。北京大学的储槐植教授在《刑事一体化与刑法关系论》中提出了刑法适用解释的概念,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是法官在个案审判中对刑法的解释。储教授的论述,为我们对刑法适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刑法适用解释,是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解释。
对于以上定义,笔者将结合一个案例进行具体地解释和说明。
案例:2000年5月4日,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刘大军杀人案”,合议庭经审理查明:1993年3月1日,河南省新县弯桥镇工人刘大军因病住院并接受输液,3月5日出院。1998年12月3日,刘大军因病住院检查,发现自己已经染上艾滋病并已经进入晚期。刘大军认为是1993年3月1日输液时所感染,十分气愤,开始对仇恨所有的人。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自1999年1月到6月,刘大军先后故意与李某等四位妇女发生性关系,致使该四位妇女染上艾滋病。2000年5月20日,新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书认定:刘大军的行为构成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一)“解释”的含义——理解即解释
传统的解释理论认为,理解就象照镜子一样,是语言文本的固有意义反映于理解者头脑中的单向的思维过程。在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知识、经验、价值倾向等主观因素对于理解的过程没有影响。但是,现代解释学理解已经认识到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理解不是主体对理解对象的单向反映过程,而是理解者的主观性因素与文本对象固有的可能的含义相互作用的过程。正如迦德默尔所说,解释对象和解释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性或历史“视界”,理解和解释不可能象传统的解释学要求的那样,让解释者抛弃自己的视界或“先见”,进入文本作者的视界。解释者对解释对象的理解和解释是一种“视界融合”过程:一方面,解释者无法摆脱自己的先见,先见构成其理解和解释的基础;另一方面,解释者又不能以自己的先见去曲解对象,对象有自己的视界,它只接纳可以接受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只有解释者和对象的“视界融合”,才能产生理解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既包括对象方面的因素,也有解释方面的因素 。
任何语言文本的含义,都不是一个精确的点,而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含义域。这个含义域里面的内容包括那些,是并不明确的,理解者必须根据个人经验和价值倾向的等作出判断,这就是对语言文本含义的解释。
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法官要将该条适用用于具体案件中,首先要理解其含义。该条中的“杀人”,是否包括通过传染艾滋病而危害他人生命的行为?法官对此的判断过程,也就是他对该条作出解释的过程。在上例中,合议庭对“杀人”的理解和解释是:该条中的“杀人”包括通过传染艾滋病而危害他人生命的行为。
(二)刑法适用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
关于刑法解释的对象,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人认为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事法律的意义内容及其适用 。有人认为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的含义及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 。有人认为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定 。
笔者认为:刑法适用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上述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刑法中的非规范性条文也包含在解释对象中,这是不科学的。刑法中除了刑法规范性条文外,还有一些非规范性条文,例如关于刑法指导思想、制定根据、刑法任务、立法目的等规定。这些规定,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作为判案的根据,因而自然就不应该成为适用解释的对象。当然,在法官对刑法规范进行适用解释时,这些非规范性规定可能会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刑法适用解释的对象。
第二种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把刑法规范与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并列起来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是通过解释其中的概念、术语、定义实现的,对规范所包含的概念、术语、定义的解释,目的和结果都是解释刑法规范的含义。
在上例中,刑法适用解释的对象就是刑法第232条关于杀人罪的刑法规范。法官对刑法第232条的解释,是通过对“杀人”概念的解释进行的。
(三)刑法适用解释的载体是刑事判决。
刑法适用解释是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思维过程本身是无形的。但是,刑法适用解释的过程可以通过判决书中的判决理由表现出来。判决理由是法官对自己解释和推理过程追溯性的描述,是整个解释过程的记录。此外,刑法适用解释的结论必然会通过判决结论表现出来。例如,本例中,判决结论认定刘大军的行为构成杀人罪,可见,对232条之“杀人”解释的结论为:它包括“通过传染艾滋病而危害他人生命的行为”
我国审判实践中,判决书中往往只记载判决结论而不说明判决理由。但是,明确、具体、有条理的判决理由,是解释者证明解释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和正当性、外界评价解释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和正当性的根据。因而从制度上要求刑事判决中必须记载规范的判决理由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例中,合议庭对作出判决的理由并没有充分说明,我们就无法判断他们是怎样得出“刑法232条之‘杀人’应包括‘通过传染艾滋病而危害他人的生命的行为’”的结论的。因而在本例中,刑法适用解释的思维过程并没有通过判决书展示出来。这样审判者既无法向人们证明他们对刑法232条的解释是正确的、正当的,人们也无法通过判决书知道审判者出于何种考虑而得出该结论的,因而就无法对这种解释过程的正当性进行监督。
(四)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是作 出刑事判决的特定人民法院及审判人员。
首先,从司法制度上讲,作出特定的行事判决的法院是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其他法律以此为依据,亦有类似规定。刑法适用解释权是刑事审判权的内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级人民法院既然依宪法和其他法律享有刑事审判权,自然就享有在个案审判中对刑法进行适用解释的权力。并且,就我国的司法实践而言,各级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判决都是以法院的整体的名义作出的,而不是以法官个人的名义作出的。因此,在制度上各级人民法院是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
同时我们要看到,刑法适用解释实际上只可能由审判中作出判决结论的审判人员行使,而不可能由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各个人民法院实际行使。因为刑法适用解释带有具有较强的经验判断性、价值判断性特点。它实际上是法官运用个人的法律理论知识、经验常识等填充抽象、概括、静态的刑法规范与具体、个别、动态的具体案件之间的鸿沟的过程。法官个人的法学理论素养、生活经验、个人人格等都将影响到他对刑法所作的适用解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依赖于法官的个人素质的高低。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人民法院,既没有生命,也就不具有任何法律知识、经验常识、人格,因此不可能实际上成为刑法适用解释的主体。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特点
(一)刑法适用解释的个案关联性特点。
对刑法规范进行适用解释的需要产生于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当刑法作为抽象行为规范指导人们的行动时,它往往呈现出逻辑自足的特点。但当它被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则往往呈现出一种抽象、笼统、模糊、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时候法官需要进行适用解释,以确定其含义、内容、适用范围后,然后才能判断它是否能包摄具体案件事实。
刑法适用解释是法官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过程中发生的。刑法适用解释的结论只具有个案适用的效力。在英美法国家,一项判决中的内容分为具有判决拘束力的部分(ratio dicta)和没有拘束力的部分(obiter dicta)。判决内容中具有约束力的部分即法官在个案审判中对法律作出的适用解释,对后来的类似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刑事判决及其所内含的刑法适用解释结论只具有个案适用的效力。
(二)刑法适用解释具有主观性的特点。
刑法适用解释的主观性首先是指它具有经验性判断性的特点。所谓经验判断,是指对于法律概念是否包含案件事实要素,必须经过法官的经验判断进行。构成要件的规定总是抽象,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形态千奇百怪。那些具体的行为形态可以包含在构成要件内,只有经过经验的判断才能确定。例如:刑法第232条杀人罪中有“杀人”的概念,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杀人”行为。某甲用毒药毒死了邻居,某乙诱使邻居到深水中游泳、导致邻居淹死,某丙则与邻居吵架,导致邻居心脏病发作而死。这些行为是否属于232条的“杀人”,需要运用经验的判断来确定。
刑法适用解释的主观性还指它具有价值判断性特点。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往往最后要通过权衡、比较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才能得出结论。例如,某甲长期受病痛的折磨,十分痛苦,某乙(医生)在某甲的苦苦哀求下,对某甲注射毒物,使他毫无痛苦的结束生命。刑法第232条的“杀人”概念是否应该解释为包括某乙的此种行为?从社会利益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因而某乙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生命首先是个人的生命,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生命的处置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法官面对这样的案件,必须通过权衡各种社会价值观,才能对“杀人”概念作出解释。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区别
刑法司法解释,按照通说的观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如何具体应用刑法问题所做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解释。
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适用解释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
(一)对“解释”一词的运用侧重于不同的含义。
刑法司法解释这一概念,是侧重于把“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活动的结果,即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一般规范性文件来理解的,刑法适用解释之所谓“解释”,则是指法官对刑法规范进行理解的思维活动。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研究,刑法学界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法律文件,研究其存在的特征、形式、结构,制定、颁布、适用,解释结论是否越权等问题展开的。对刑法适用解释的研究,则应该主要着眼于研究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刑法规范的含义。
(二)权力来源不同。
刑法司法解释权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它是独立与国家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的一种独立的权力。刑法适用解释权力是国家刑事审判权本身固有的、内在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效力不同
刑法司法解释具有一般规范性特点,对各级司法机关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刑法适用解释的结论只具有个案适用效力。
(四)刑法司法解释由于是一般规范性文件,是一种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法” 。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往往仍显得较为抽象、概括、模糊,从而需要对其进行适用解释。
例如,最高法院《关于审判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7)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一条司法解释看似明确,却留下了以下疑问:一是入户盗窃之“户”,是专制民宅还是包括单位用房,即入“户”是否就是入“室”,在抢劫罪中,入户抢劫与入室抢劫有别,这一区别在盗窃最终是否存在?二是一年内实施了三次入室盗窃或扒窃行为,但有一次没有得逞,是否成立多次盗窃?三是年内实施了三次入室盗窃或扒窃行为,但前两次已经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过,是否还成立多次盗窃,如成立,是否有重复评价之嫌疑。四是虽实施了三次盗窃行为,但所盗窃得的现金分别为一元、五元、拾元是否构成多次道歉窃,倘若肯定则刑法可能过于苛严,倘若否定,是否有回到了“唯数额论”的老路上 ?
对于这些问题,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时,必须作出回答。例如,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户”是指民宅。某甲一年之内四次潜入一工厂堆放产品的大院里进行盗窃,是否属于该司法解释中的“入户”盗窃?从该司法解释看,并不清楚。因而法官在审判中还需要对“户”进行适用解释,确定它究竟是否包含单位用房。又如,某乙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了三次,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未得逞,第三次只有预备行为,没有着手实施。某乙的行为是否属于该条司法解释中的“扒窃三次”呢?法官在审判中就需要判断“扒窃”一词仅仅指既遂行为、还是亦包括未遂、预备行为,判断的结果就是他对“扒窃”的理解和解释。
第三章、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之制度化
第一节 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制度化的思想基础
一、立法权、司法权分立之相对性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国家必须分权。“每一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一是立法权力,二是关于国际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是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我们将后者称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如果立法权同司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置于被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三权分立思想本身是合理的,但是绝对严格的三权分立理论则将三权分立思想绝对化,认为法官只能根据既定的法律、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判案,法官不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有个人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纯理性的观念无视法律运行的内在实际规律,早已受到了学者的批判并被证明是不合实际的了。
首先,绝对严格的三权分立思想对三权分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理解,只看到分立而没有看到制衡的一面,分立是手段,制衡才是目的。制衡之意就是在于当一种权力过大篡越其他权力时,其他权力予以制止,使三种权利保持平衡,保证国家的协调发展。制衡是运动中的平衡。保持运动中的平衡除制止某一权力过大之外,应当包括对另一权力过弱或出现缺陷时的补充。三权之中,司法权最弱,因此,司法权以自己的职能范围(法律解释)填补使其行政权过弱而受损的某种缺陷。这种填补对保持三权的动态平衡是必须的。
其二,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必要的手段,这是司法的实际规律,绝对的三权分立理论由于过于理想化而与实际脱节。凯尔逊从纯粹法学的立场曾指出:“在规范的等级体系中,基本规范只创立法律,而不实施法律。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个别规范并不创立任何新的规范。除基本规范和最终的个别规范外,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既实施法律又创立法律。较高级的规范就可以创立若干专门的‘框架’,使适用法律的机构享有自由裁量权。因而,立法者与法官并无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较高级的规范对于法官来说,只是在他可以行动范围内的一个‘框架’ 。”
其三,各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的三权分立都是相对的,美国宪法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与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但是它们并没有绝对化,如宪法第1条第3款第2项规定,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而按宪法的精神,最高法院对宪法和法律有解释权。又如,法国从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新颁布的《戴高乐宪法》,改变了过去的分权制度,三权分立不再严格,标志之一就是总统享有立法权。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看,各国的三权分立都有三权相互滲入的一面。立法权不仅由立法机关行使,行政部门也有立法权。这是因为在现代国家中基于六项原因,委任立法不可避免:1、议会议事时间不足以应付巨额的法案。2、议事主体过于部门技术化。3、不可预测的偶发事件。4、立法机能得不偿失弹性问题。5、立法机关欠缺试行经验造成困难。6、有关紧急权问题,须赋予行政机关紧急立法权 。上述这些理由大部分也适合于解释法官为什么应该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力。
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相对性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刑法思想史上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理解经历了从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到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过程。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坚持绝对的成文法原则,要求立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和刑罚规定必须绝对明确,禁止法官对刑法进行适用解释,禁止设立不确定刑。而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不再要求刑法规范的规定必须绝对明确,承认法官对刑法进行适用解释的存在及其合理性,承认相对不确定刑之合理性,只禁止绝对不确定刑。
今天,我们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理解,必须坚持相对化的立场。
(一)从刑法立法上看,现代各国(包括我国)在立法上,都不再要求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绝对明确具体。为了使刑法能够灵活的对付各种复杂的犯罪行为,刑法立法者一般都仅仅规定具有一定概括性、抽象性的犯罪构成。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刑法中有大量的“其他方法”、“情节严重”等规定。在这种立法方式下,法官必然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力。
(二)从思想渊源上看,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发源于英国的《大宪章》的思想。1215年英国大宪章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者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它所确立的是一种“只有依法律才能剥夺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制原则”,而不是成文法原则 。它根本不排斥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思想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基础,并以此否定法官对刑法的适用解释的权力。但是,正如泷川幸辰所说,“将分权理论作为罪刑法定主义根据的理由是极为不充分的,分权理论最终完全封锁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并把触及法律也视为一种犯罪。向立法者要求完美无确的法律,这无异于期待神的力量才能实现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立法者能够把犯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全部洞察清楚,正因为如此法律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才成为必要 ”。此外,心理强制理论亦由于排斥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权而不再被认为是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渊源。
(三)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容上看,明确性(definiteness)作为现代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源生原则,并不排斥法官对刑法的适用解释。
什么是明确性原则呢?日本学者西原春夫从可预测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明确性的基本含义是指什么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对于一般国民来说,必须是可以加以预测的。在西原春夫看来,刑法的明确性所包括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都不排斥法官的适用解释:
(1)罪之明确性。犯罪的成立要件的明确性含有容许解释的余地。对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是迫不得已的,只要解释限定在一般国民可能预测的范围之内,应该认为并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只有过于抽象而使解释的界限无法被预测的法律条文,在罪刑法定主义上才是不被允许的。可见,罪之明确性并不排斥法官的适用解释,只是解释必须有一定的界限。
(2)刑之明确性,在法定刑上设定一定的幅度是使量刑成为可能的必要措施。但是绝对的不定期刑(例如仅仅规定“处予徒刑”而完全不规定期限的自由型)因其使宣告刑的预测变得十分困难而不能被承认。不过,相对的不定期刑(法律规定刑期的上限与下限,法院宣判后,实际上执行的刑期则委于执行机关裁量决定)在刑期的上限与下限之间的幅度并不特别大的情况下,不一定理解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 。
可见,现代的罪刑法定主义是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无论在“罪”之确定还是在“刑”之确定方面都是不排斥法官对刑法的适用解释的。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制度化的实践
一、法制实践的困境
我国刑事立法由于在很长时期内坚持“宜简不宜繁”的立法思路,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立法给法律的适用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的空间。例如,我国刑法中大量的使用“其它方法”、“情节严重”、“严重后果”“数额较大”等概括性用语;又如,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包含着“定量”因素,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各种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中,对于如何确定“情节显著轻微”的量的标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规定。
刑法立法留下了广泛的解释的空间,对于这一空间,只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和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的刑法适用解释来填充。在实践中,我国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各种形式的刑法司法解释来填充立法留下的空间的。但是刑法司法解释对刑法的解释毕竟是有限度的,并且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本身亦不完全明确、具体,因而各级法院及法官实际上也在享有着较为广泛的解释的空间。
对于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解释尚未明确的地方,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处理?制度上对此没有规定。理论和实践中许多人认为法官不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每当遇到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他们就认为是立法的不足,或者是刑法司法解释没有解释清楚。因此凡是遇到在法律适用上稍有疑难的问题,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司法解释。但是,无论司法解释如何细致,一般性、抽象的规范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差距是永远无法填平的,各级法院于是进一步报请司法解释。导致的结果是最高人民法语的各种刑法司法解释不尽其数,各级法官最后几乎不是在依据刑法审判,而是依据司法解释进行审判。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恶果是:
首先、凡遇疑难案件必报请司法解释,影响了各级法院的审判效率;也使最高人民法院为大量的司法解释所困,几乎从一个审判机关蜕化为一个以司法解释为主要任务的机关。
其次、各级法院完全依赖于司法解释进行审判,导致审判人员的素质难以提高。审判人员没有能动司法的压力,就没有提高法学素养的动力。由于有大量的司法解释存在,而且司法解释不明确的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报请司法解释,因而审判过程不需要审判人员有良好的法学素养,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也难以提高其法学素养。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审判人员的素质一直难以提高。
再次、由于在司法制度上和刑法理论上都没有明确法官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导致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多从法律立法和司法解释完善的角度进行,而从刑法适用角度进行的研究则相对要少。因而,刑法解释学理论不发达,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变成了“刑法规则完善学”和“刑法注释学”。最终的结果,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脱节,难以为审判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
二、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之制度化
(一)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之制度确认
各国在对刑法适用解释权力规定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有些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权对法律做出解释,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73条规定:议会有权解释法律,但这并不妨碍法官对这些法律作出自己的解释。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02条规定审判人员和人民陪审员在履行职务时是独立的,只服从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审判人员和人民陪审员有义务服从法律和其他有关条例,并根据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解释法律和法律条例 。
二是也有不少国家只规定了普通法院的司法权,并没有在宪法中把它作为一种权力加以规定。我国即是如此。如我国宪法及其它法律都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对于各级法院及法官是否享有法律适用解释权力,法律并没有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宪法所规定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理解为:该条在授予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同时,也授予了法官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是因为,刑法适用解释是法官在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发生的,刑法适用解释权力可以认为是刑事审判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宪法授予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刑事审判权,自然也就授予了他们法律适用解释权。
(二)刑法适用解释权力范围之制度确认
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是不完备的,因而留下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对于这一解释的空间,是否完全就是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进行适用解释的空间?亦或是,各级法院在此空间里所遇到的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都应该报请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对此,我国现在的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也不统一。那些案件报请司法解释,那些案件由法院自己处理,似乎没有统一标准。
笔者认为,应该将法官享有的刑法适用解释权力的范围制度化。对于刑法适用解释范围,应该划定的原则性界限为:1、对于各个地方普遍发生的案件,如果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着疑难问题,应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2、对于实践中很少发生的、不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如果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疑难问题,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应该在审判过程中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谨慎地进行刑法适用解释。这里,所谓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着疑难问题”的案件,即上文中论述过的疑难案件,既包括法律概念或用语本身含义模糊不清的案件(语言解释存在争议的案件),又包括按照法律概念或用语的一般含义严格适用可能导致判决结果不合理不公正的案件(处理结果存在争议的案件)。对这些案件,一般需要运用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进行扩张解释或者缩限解释,对此以下章节中将详细论述。
为什么作上述的划分呢?
笔者赞同储槐植教授的一个观点,即我国的刑法立法实际上是由三个不同层次的立法阶梯共同组成的,即宏观立法、中观立法和微观立法。宏观立法就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刑法,包括刑法典和特别刑法,刑法立法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中观立法就是最高司法机关在此空间内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也不是详尽、完备的,仍然留有解释的余地。微观立法就是各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此范围内所作出的刑法适用解释。
笔者认为,在这种法制结构下,将刑法司法解释权力和刑法适用解释权力作如此划分有如下好处:
(一)从制度上确认各地法院对一定范围内的疑难案件享有刑法适用解释权,可以缓解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大量司法解释的压力;同时又可以使各级地方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保持一定的压力,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审判人员的素质才会提高。
(二)对于实践中发生得较少、不具有普遍性的疑难案件,由于各种矛盾尚未完全暴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得不充分,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也存在广泛的社会分歧,因而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普遍效力的司法解释是不合适的。各级地方法院对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社会观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刑法适用解释,有利于实现个别公正。而且由于案件发生得较少,由地方法院进行刑法适用解释,不会导致明显的法制不统一。
例如,对于给他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杀人”?在怎样的条件下构成“杀人”,怎样的条件下不构成“杀人”?对此,刑法没有规定,刑法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笔者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虽然存在,毕竟不是普遍发生,而且对这种行为性质的认识也存在广泛的分歧。在矛盾没有充分暴露之前,作出一般规范性的司法解释是不合适的。
(三)对于实践中普遍发生的疑难案件,由于该种性质的行为的各种样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较为充分的表现出来,人们对该种行为的认识也更深刻一些,各地方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最高司法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不仅可以保证解释的科学性,也有利于维护各地方法制的统一。
例如,我国刑法第280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伪造、贩卖伪造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该种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也较为统一。那么,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伪造事业单位印章”呢?对此,各地法院以前有不同的认识,实践上也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7月了《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22号),对此作出了统一的规定,规定该种行为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这样,就维持了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法律渊源
在法学理论中,法律的渊源,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法律价值的法律资料、材料和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如理论学说、正义观念等。法律的渊源可以分为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法律的正式渊源,是指具有规范效力的法律权威性文件。我国刑法的正式渊源有:刑法典、特别刑法、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法律的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值得考虑的材料,而这些资料和值得考虑的材料尚未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或者至少是明文的阐述与体现。博登海墨认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至少包括: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和习惯法 。
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是指对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具有意义的法律文件、资料、材料和其他因素。也就是,当法官在对特定的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他应该考虑那些方面的因素。
例如,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终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有一具体案件如下:被告人某甲于深夜翻入一户人家屋里,见一妇女睡在床上,欲行强奸。待走近后,发现该妇女是旧日的密友,于是羞愧难当,急忙逃走。面对这个案件,法官应该如何理解刑法24条中的“自动”这一概念,它是否包括某甲的该种情况?法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考虑那些方面的因素呢?他至少应考虑:1、刑法上下文的规定,如刑法第23条之“未遂”是如何规定的,被告人的情况是23条之“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呢,还是24条之“自动”?2、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对此有没有加以规定?3、刑法学理论。刑法解释理论上对中止犯的“自动”是如何解释的?4、一般人的观念。按照一般人的认识和语言习惯,这种情况是“自动”吗?法官可能还会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凡此种种,都是法官在理解和解释24条之“中止”时所要考虑的,这些因素都是对解释结论有重要意义的,因而都是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
在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渊源包括那些呢?
第一节 正式的法律文件
一、刑法(刑法典、特别刑法)、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
(一)特定的刑法规范及其法律概念往往只有在上下文整体中才能确定其含义,对特定法律规范的解释必须关注其上下文,以确定正确的含义。例如,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处……”,但是,在强奸妇女过程中过失致其死亡的,是否属于第233条规定的范围呢?结合第236条第三款之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进行考虑,才能确定233条之刑法规范的行为。
(二)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文件是特定机关对刑法作出的有权解释,法律适用者在理解和解释刑法规范时必须遵循。 二、行政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法规
刑法在性质上是其他法律的最后“保障法” ,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足以制裁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大行为时,才动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因而,刑法规范对犯罪构成的规定与其他法律对违法行为构成的规定往往有相通之处。实际上,大量的刑法规范(主要是行政刑法规范)规定行为构成犯罪以违反相应行政法律法规并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在一些行政法律法规中,对违法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法规范,或者规定依特定刑法条文处罚。因而在对有些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法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根据该条,认定行为构成非法批准用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必须以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为要件,而行为是否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必须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和规章 。此外,一些刑法规范含义的确定需要参考行政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58条规定的重婚罪中,对?
爸鼗椤钡娜隙ū匦氩慰蓟橐龇ǖ墓娑ê妥罡呷嗣穹ㄔ憾曰橐龇ǖ乃痉ń馐汀?
第二节 非正式的法律资料
非正式的法律资料在我国主要是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和其他政策。
在我国,刑事司法必须考虑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和其他政策。这是因为,我国刑法立法强调对党和国家基本政策和刑事政策的体现。既然刑法立法体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政策,那么在解释刑法的时候,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从党和国家的政策出发,去揭示刑法规定的含义。党和国家政策作为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的根据,主要体现在:
(一)有些刑法规定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阐明其含义。
例如,1979年刑法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从该刑法规范制定时的经济体制讲,当时基本上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圈子,强调国家对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对投机倒把罪的解释就必然会把倒卖一般物资牟取暴利等行为包括在投机倒把行为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破坏了国家对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管制,是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所不允许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的经济政策作了调整,宣布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除少数由国家统一控制的特殊商品外,商品的价格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行为就不能视为投机倒把罪。虽然当时立法、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新的规定,但学理上认为应将投机倒把罪理解为不包括该种行为 。
(二)有的刑法规定需要根据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进行或者限制或者扩展解释。
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刑事政策可能会对于相同的刑法条文的含义、范围等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于理解、解释或适用刑法条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刑事政策提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判断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这就成为判断某些具体犯罪(主要是行政犯)的罪与非罪,以及判断某些犯罪的重罪与轻罪的重要依据。而且,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式发生变化的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形势政策对于某一类或者某几类犯罪进行评价的严厉程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其影响或指导下,司法对于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评价及其处罚轻重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一段时期中,由于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猖獗,刑事政策就地取材确定对这些犯罪要依法“从重从快”、“从重从严”惩处的方针。司法实践中对这些犯罪的犯罪构成、刑罚的理解解释必然也受其指导 。
第三节 法学理论知识与一般社会观念
(一)刑法学理论知识对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正确的解释刑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刑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对现行刑法进行科学的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是刑法学研究的意义和生命。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诚然,刑法学研究内容中,不仅包括对现行刑法的解释研究,而且包括对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犯罪的本质、刑事责任的根据、刑罚的目的等,又包括对现行刑法的解释。但是,对现行刑法进行科学的解释是刑法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和生命所在。这是因为,刑法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其动因源于司法实践中对现行刑法进行正确理解和解释的需要,这些问题本身也是在人们长期的理解解释刑法的过程中提炼和积淀而成的。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刑法解释的实践 。正如有学者所说:“刑法学是‘体’而解释论(或称解释学)是‘用’,有‘体’而无‘用’,则‘体’为僵尸,无由体现其作用,刑法学之所以成为学及其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都须通过刑法解释论来实现。”“不存在没有解释论的刑法学或刑法解释学,甚至可以说,解释学或解释论就是刑法学或者刑法解释学本身,至少是重要组成部分 ”
从刑法适用实践的角度来看,将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实践是一种理论性、技术性很强的实践活动,需要法学理论知识,特别是刑法解释学知识的指导。刑法中有许多法学专门术语,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对其含义法学理论上往往有深入研究,法官在适用刑法时需要以法学理论知识为指导来理解这些术语。刑法中另有一些普通用语在刑法上有特定的含义,对其在法律上特定含义的理解也需要刑法学理论的指导。如未遂的“着手”、故意的“明知”等。
(二)一般社会观念。
一般社会观念,如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经验常识、道德善恶观念等,在刑法适用解释中有重要意义。
1、刑法中的各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形象是立法者根据经验判断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犯罪活动的抽象,因而在刑事司法中,社会经验常识也是法官判断具体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基本的根据。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杀人”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形象,具体生活中有投毒杀人、用刀砍杀、电击杀人、饿死婴儿等等无数中无数种杀人或类似于杀人的案件事实,如何判断这些具体案件事实是否是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杀人”?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方法还是要通过经验常识的判断。
2、对于某些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评价标准。例如,父亲杀死作恶多端的逆子,兄长处毙危害民众的弟弟等非法杀人行为,通常被人民群众认为是“大义灭亲”、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有的社甚至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类非法杀人的评价,我们在解释刑法第232条中“情节较轻”故意杀人时,应将这一类非法杀人包括其中。
第五章 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
第一节 主观解释理论
主观解释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准确的表达了立法者当时的意思。法律的字面含义是重要的,因为需要根据字面含义推知立法者的意思,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推定,字面含义是立法者意图的表达。但字面含义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不仅在于立法文字的含义要根据立法者当时的意图确定,而且在于,如果有证据表明文字的通常含义同立法者在立法时意图表达的含义不一致时,就应该采用其次要的但与立法者意图相一致的含义,哪怕这样理解回牵强附会,但由于是必须的因而是合理、正确的。由于这种解释理论以立法者当时的意思为认识的目标,企图达到立法者当时的主观心理状况,所以被称为主观解释理论,又称为立法者意思说。
主观解释论的理论根据是:其一,只有立法者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立法行为是立法者的意思行为,立法者通过立法表达它们的看法和企图,借助于法律实现他们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因此只有立法者知道得最清楚。其二,为了确保法律的安全价值,立法者的意思是一种可以借助立法文献加以探知的历史事实,只要法律解释取向于这种可以被探知的立法者的意思,法院的判决和决定就不会捉摸不定,因此,贯彻主观解释说可以确保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其三、基于三权分立的原则,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的制定,法院的职能只能是依法裁判,立法者的意思是法律适用上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法律解释应以探求立法者的意思为目标。
主观解释论后来在旧主观说的基础上形成现代主观说,现代主观说与旧主观说的区别在于,不再如旧主观说那样探求立法者于立法时的心理学上的意思,而是探求法律规范背后并与之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利益状态及其衡量,以尽量扩充法律规范的意义内容,现代主观说不再如旧主观说那样迷信法典完美无缺,而是假定广泛的法律漏洞领域的存在,但对于法律漏洞原则上应推测立法者的评价以进行补充,在无法推测这种评价时,则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评价及自己的评价,进行补充。此说将制定法的历史的解释与法官的规范创造功能加以调和,以兼顾法律的安定性和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对法学界及实务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
第二节 客观解释理论
客观解释理论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即与立法者相分离而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这种独立的意义是通过将具有一定意义域的文字,运用一定人群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法规则加以排列组合而形成的。立法者于立法时主观上希望赋予法律的意义、观念及期待,并不具有拘束力,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是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内部的合理意义。故此,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事实上的意义,而在于探究和阐明内在于法律的意义和目的。这种探究、阐明法律内部合理意义和目的的活动并不时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律内部的合理意义和目的也会发生变化,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在法律条文语义可能的若干种解释中,选择现在最为合目的之解释。客观解释论者强调,法律解释总是关于现在的解释,而且与目的论的解释相结合。同时,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漏洞是不可避免的,法官解释法律有规划创造规范、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
客观解释理论的根据在于:其一、一个具有意思能力的立法者并不存在。法律只草拟、制定,历经各种机关,何人为立法者难以确定。意思不一致时,应以何人为准,存在疑问。其二、法律与立法者的意思并非一体。具有法律效力的,系法律形势表达于外部的表示意思,而非所谓立法者主观的意思。其三、受法律规范之一般人所信赖的,是存在与法律规范的合理的意思,而非立法者主观的意思。其四、客观说最能达成补充或创造法律的功能。倘若采用主观说,则法律之发展将受制于“古老的意思”,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基本立场
一、一种正确的立场:折衷说
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思想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又都失之偏颇。具体而言:主观解释思想强调立法原意是存在和可知的,注重法律的稳定性和自由保障机能,是值得肯定的。但主观解释思想完全无视客观现实的要求,无视法律的公平价值,则是需要否定的。相反,客观解释理论强调根据现实的需要寻求法律的合理意义,注重法律的公平价值和社会保障机能,但是否认立法原意的存在及其可知性,无视法律的稳定和自由保障机能,则是错误的。
主观解释思想与客观解释思想的折衷,是现代刑法解释思想的基本立场。例如,上述现代主观解释思想实际上就是以旧主观解释说为基础、吸收客观解释思想后的一种折衷。又如,我国台湾刑法学者认为:“刑法之解释宜采主观与客观的综合理论,即:原则上,采主观理论,对于刑法条款之解释仍应忠实的停留在立法时之标准原意。惟如有足够之理由证实立法当时之价值判断,显因时过境迁,而与现阶段之公平正义、社会情状与时代精神等不相符合时,则应例外地采用客观理论。并且,时间因素在刑法之解释上,亦扮演一重要角色:对于新近公布施行之刑法条款,则以主观解释为主,就法律条文之实体内容,以事解释。反之,对于公布施行已久的刑法条款,则因法律诞生至法律适用,已经一段长的时间,故应着重客观意思,以为解释 ”。
笔者认为,刑法解释理论采折衷说的立场是正确的。这是因为:
(一)应该承认,法律规范的立法原意是存在和可探知的。
任何立法活动都是立法者有意识的活动,立法活动的成果即法律规定,是立法者借助于文字符号这种载体所表达出来的主观上的意义,所以,任何法律规定都具有立法者所赋予的原本意义。立法原意对于立法者来说是主观的但对于解释者来说则是客观的。立法原意是可探知的,不是说立法时各位立法参与者头脑中抽象的思想和情绪是可探求的,而是说立法者借助于文字符号这种载体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是可以通过分析立法相关资料、立法前后社会环境和重大事件等而探知的。
(二)刑法的稳定性和公正价值,或曰自由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不可偏废。
刑法的稳定性是最基础的价值,而公正价值则是法律最高的价值。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否则就会使广大的公民毫无安全感,公民权利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刑法是所有法律中制裁措施最严重的,刑罚权之发动事关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的剥夺,因而应更为谨慎,从而刑法的稳定性价值较于其它法律更为重要。但是,法律的最高价值在于公正,或曰正义。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有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说,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有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 。可见,公正的最高境界是个别公正,这种个别公正只有通过发挥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才能实现。
二、折衷的具体立场
关于主观解释思想与客观解释思想折衷的具体立场,笔者亦基本赞同上述台湾学者的观点。但结合我国大陆的司法制度的实际,宜作具体分析,具体而言:
(一)对于刑法立法解释和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刑法司法解释,应在兼顾主观解释理论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客观解释的立场。
首先,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层出不穷。社会的急剧变化引起人们观念普遍发生变化,一些行为在旧的社会环境下被认为有或者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则被认为没有或者仅仅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但是,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必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而,对于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大胆地进行目的论解释,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一般规范性的特点,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因而依客观解释思想得出的解释结论会被统一的适用于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不会造成法制的不统一。
其三、有学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大量采用客观解释论立场会侵犯立法权,但是,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绝对分离在理论上早已被证明不符合法律运行之规律,在各国法制实践中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况且,任何思想观念都产生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时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 。以绝对分权的抽象的观念否定司法解释可以有一定限度的创造性解释是不正确的。
(二)对于刑事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刑法、刑法立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解释,则宜以主观解释为主,兼顾客观解释的立场。
具体而言,应首先以主观解释立场进行解释;当解释所得结论不合理时,如果是实践中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应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如果是较少发生的个别案件,可自行根据客观解释论作出合理结论,并说明判决理由。这是因为,首先,依客观解释理论进行的解释有较强的造法倾向性,而目前我国司法制度不尽完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因此普遍依客观解释论进行刑法适用解释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次,对于司法实践中普遍发生的案件,需要依客观解释论进行解释的,由最高法院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司法公正。
第六章 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
第一节 刑法解释方法的种类
按照刑法学界有关学者的研究,刑法解释的方法包括:
(1)文义解释方法,指如果法律语句本身是清晰的,不回引起歧义和荒谬的结果的话,就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规范所用词语的通常含义来解释。
(2)系统解释方法,指联系整个刑法典、单行刑法、非刑法法律中的刑法规范的相关规定,对刑法的某一规定的用语的含义予以阐明的方法。
(3)历史解释方法,指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极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的方法。
(4)扩张解释是法律条文字面意义失之过窄,不足以表示立法真意,故将法律条文作扩大解释,以求正确的阐释法律条文的含义的解释方法。
(5)缩限解释,指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失之过宽,不符合立法真意,故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限制在核心部分,以正确阐释法条的意义和内容的解释方法。
(6)当然解释,指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依照法律的精神该事项实际上已包含于条文规定的含义之中,故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的解释方法。《唐律·名例编》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是对当然解释的规定。《唐律疏议》对“举重以明轻”的解释:“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即,主人杀死夜晚无故进入其家的人不予论罪,所以,如果主人将夜晚无故闯入其家的人打成折肢伤害,当然也不判罪。
(7)目的解释,指根据立法目的,阐明刑法条文含义的解释方法。例如,我国《刑法》第295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的,处……”,本条中的“传授犯罪方法”指传授一切犯罪方法,还是传授故意犯罪方法,还是指传授严重的故意犯罪方法呢,从立法目的上考察应是传授严重的故意犯罪方法。
(8)合宪性解释,指依照宪法和其他位阶较高的法律,解释位阶较低的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
(9)比较法解释,指引用其他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或者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项参考因素,用以阐释被解释的条文的意义与内容的一种解释方法。例如,在我国《刑法》未修改之前,第126条规定:“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害的……”,但条文中对挪用去向并没有特别要求,究竟是归集体或归个人使用亦或兼而有之,并不明确。进行比较解释,《关于惩罚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第1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可知《刑法》第126条中之“挪用仅仅指挪为集体它用,不包括挪为个人所用 。
(10)社会学解释,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和内容的一种解释方法。例如,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但是,在夫妻关系存续其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能否构成强奸罪呢?如仅从刑法该条看,完全可以。但根据社会学的解释方法,一般情况下,丈夫不能构成强奸罪的主体。
第二节 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
上述我国刑法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刑法解释方法,虽然极赋启发意义,但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各种解释方法的视角标准各不相同。其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刑法适用解释方法只有文义解释方法、法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其他解释方法或者是大致落入这几种方法的范畴之内,或者只是作为辅助性的方法而不具有独立的实用价值。
例如通常所谓的扩大解释和限制解释只是基于解释后果对解释的分类,而根本不是一种方法,即无法指导具体的解释。它无法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作出扩大或限制解释,它既必须基于文义解释,又必定要考虑到立法原意,目的和实施的后果。当然解释不可能抛弃对立法目的和判决的社会后果的考察。比较法解释同样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参考因素,孟德斯鸠早就说过:相似的法律不一定出自相似的动机,看来相同的法律有时实在是不相同的 。只有在其他解释得以成立的前提下,比较法解释才具有支持性的证据力或证否力。系统解释方法是把法律文本作为一种语境,而根据语境的解释方法,是文义解释方法和法意解释方法的辅助解释方法,因为所谓平意义解释方法中的平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语境决定的,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意义。脱离具体的语境,很多词语都变得不明确、没有“平义”了。同样,法意解释也离不开语境。当法官或律师试图发现立法资料或其他学者的解释,例如立法的辩论记录,立法者个人的日记通信,立法前后社会环境和重大事件,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所有这些材料都用来证明某种意图是立法的真正的、原初的意图 。社会学解释实际上是一种考虑解释的社会效果的目的解释。
因此,笔者将刑法适用解释的方法归结为文义解释方法、法意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来加以分析。
文义解释方法和法意解释方法源于主观解释理论。主观解释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立法者的立法原意。但是,立法原意是什么呢?立法原意又如何体现呢?早期主观解释论认为立法原意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客观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解释法律意味着寻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客观存在的精神状态,由于立法时立法者的精神状态是不可捉摸的,这种主观解释理论早已被淘汰。现代的主观解释理论不再认为立法原意是那种立法时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不可捉摸的精神状态,在如何认识立法原意问题上,现代主观解释理论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立法原意是立法者通过正式的法律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立法意图,探求立法原意不能参考除成文法以外的其他的立法时所留下的资料,因为它们不是正式的法律,根据这些资料探询立法原意有违法律的自由保障原理。例如在英国,法院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律师在解释论点中引证议会辩论记录、议会委员会报告的立法准备材料的学说 。另一种认为,认识立法原意需要参考立法时留下的所有的立法资料,既包括正式的法律的文字,也包括其它的立法资料,如法律草案、立法时的各种文件,各立法者的法律观点,对立法时所针对的社会状况的记载等。非正式的立法资料与正式的法律在探询和证明立法原意时有同样重
要的地位。这两种观点发展至今,分别表现为文义解释方法和法意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方法则源于客观解释理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法律适用解释必须符合实际的社会生活,因此,客观解释之所谓“客观”在词义上是指客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客观解释论看来,法律只有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才能保持活力,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的表现,是法律适用时社会群体的代言人。这一切都要求法官考虑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的目的,相对自由的解释法律,以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 第三节 刑法适用解释方法的运用
一、关于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观点
刑法适用解释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正确的解释方法获得法律语词在具体案件中的正确意义和内容。解释方法的运用只有遵循一定的优先性原则的指导,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原则,我国学者梁彗星认为:1、对法条的解释,首先应采用语义解释方法,如解释的结果可能为复数,则继之以论理解释的方法(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2、作论理解释时,应先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以探求法律意旨,进而运用扩张解释或缩限解释或当然解释以判明法律的意义内容,如仍不能澄清法律语意的疑义,则进一步作目的解释以探求立法目的,或者在依上述方法初步确定法律意义的内容后,以目的解释进行核实,最后做合宪性解释看是否符合宪法的基本价值判断。3、经论理解释仍不能确定结论,可进一步做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4、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的结果只有在不超过法条语意可能的范围时才能作准。5、经解释最终仍存在相互抵触的结果,则应当进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从中选择出更具有社会妥当性的解释结果作为结论 。
刑法学者李希慧认为刑法解释方法大体应遵循以下规则:一是文理解释优先。二是单一规则。即通过文理解释,刑法规定含义明确,不存在歧义,就不需运用论理解释的方法。三是综合规则,即在解释刑法规定时,既运用文理解释,又运用论理解释。四是论理解释优势规则。即对刑法规定的同一用语进行解释时,在文理解释的结论与论理解释的结论相冲突时,应取论理解释的结论 。
二、刑法适用解释方法的运用
上述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但对于刑法适用解释而言并不一定具有可操作性。笔者认为:
(一)平义解释方法应是我国各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当中的首要的刑法适用解释方法。
平义解释方法是法官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运用的首要的解释方法。这是因为:首先,审判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是常规案件,只要依照平义解释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可行的,那么平义解释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在寻求其他的解释方法,当然这不排除用其他的解释方法来印证平意义解释方法运用所得的结论。其次,平义解释方法是选择和运用其它解释方法的基础。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非常规案件,虽然运用平义解释方法往往不能得出唯一正确的解释结论,但是所得出的数个解释结论为法意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提供了选择的基础。
平义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普通含义解释方法和专门含义解释方法。普通含义解释方法是指,如果法律规定使用的是普通语词或词组,而且在普通语言中是明白的,那么除非有充分理由作出其他不同解释,就应当以普通说话者的理解为标准作出解释,如果可供选择的普通含义不止一个,那么在解释中应该优先考虑和采用相对比较明显的普通含义。专门含义解释方法是指如果法律规定所使用的是专门语词或词组,或者是具有专门含义的普通语词或词组,那么就应当从专门含义的角度进行解释 。
运用普通含义解释方法,首先要确定该用语的普通含义,也即字典含义。在汉语中,字词的字面含义往往是有多个,这时候,需要运用语法解释方法、根据字词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来确定应采用那一种字面含义。如果仍然不能确定,这时候应该运用系统解释方法、据上下文系统的关系来确定那一种字面含义是唯一合适的或者比较明显的普通含义。
运用专门含义解释方法时,词或词组是否具有专门性,是不是在专门意义上被使用,通常可以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它在法律中使用的历史来确定。专门法律术语的专门含义,通常可以经由经过法律训练者来识别,但是,这种术语的相关历史也可以是决定性的。具有专门含义的非法律专门术语的专门含义,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不明显的,如果不明显,就需要印证或证明 。
(二)当运用平义解释方法得出的解释结论仍然不确定时,应运用法意解释方法进行解释。
法意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当时的价值判断,即以立法者的意图来解释法律规范中的边缘含义。立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是运用法意解释方法解释法律的主要依据。法意解释方法的实践基础是,每个社会有特定的解释共同体,这种解释共同体是指对某种事物达成共识的人的群体,它具有历史的延递性,因为每个时空的文字与文字相关的文化背景回随着时空的演进而延递;后代的司法者是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立法背景材料并熟知当时的立法内幕,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可以探求得到立法的初衷,从而保证法律适用的时空上的公平一致,不至于使同样的案件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而有迥然不同的判决 。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运用法意义解释方法探求立法原意是可能的。首先,我国刑法制定和修改的时间都不太长,立法与司法的时空间隔不远,解释共同体连贯,甚至具有同一性,寻求立法原意义是可行的。其次,我国立法机制较为简洁,不象西方国家那么复杂。再次,大量的立法背景资料如草案、修订说明、各种学术争论等是可以获得的。
运用法意义解释方法时候,首先应该尽量运用公开公布的立法背景资料,或至少应该保证所使用的立法背景资料是切实可靠的。其次要正确的运用各种立法背景资料,要正确地分析法律规范设立或修改所针对的社会状况、针对该状况的各种立法或修订观点、以及立法者所采用的立场及其原因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探寻出立法原意。
法意解释方法只有在运用文义解释方法得出的解释结论是复数结论时才运用,换言之,文义解释方法具有比法意解释方法优先适用的地位。法意解释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从运用文义解释方法得出的复数结论中确定正确的结论。
(三)当运用平义解释方法或法意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明显的不符合常理时候,应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以获得合理的结论。
法官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候,面临的难题是在具体案件中识别出其中蕴涵的社会公正和时代精神。这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而不是形式逻辑问题,它需要法官运用各种综合能力加以判断。如何发现法律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实践理性而非科学分析和逻辑推理。实践理性不是一种单一的分析方法甚至不是一种有联系的方法,它包括内省、想象、常识、移情、说话者权威、类比、前例、惯例、经验、知觉、期望等 。
实践理性混杂而不够严格,但在逻辑或科学无能为力时候它常常是我们进行价值选择的重要工具。例如:贵州曾发生三个刚成年的青年打死三条名贵的狗的案件,法院如何把刑法中的盗窃罪适用于本案件中,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盗窃罪中的“财产”一词,若将该狗的价值作为法律规范中“财产”的价值,三人重罪无疑,若将狗肉的价值作为财产的价值,则三人可以从宽发落,该案审判中法官的价值发现是基于这样一来的一种判断:人命比之狗命如何?于是法官作出了从轻的判决。
实践理性的方法为法官在为法官在目的解释中寻求法律的价值取向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当中,法官可运用逆推法,把法律规范可能具有的含义一一罗列,然后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得出数个结果,经过比较,如果认为某个结果是合理可取的,那么导致这个结果的解释则是该法律规范所包含的价值判断。
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其实践基础:首先,司法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应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具备强烈的社会正义观以及公序良俗的内心判断能力。其次,应具备法官独立审判的条件,使法官不会因为法律之外的个人利益等非法律因素的考虑而滥用目的解释方法。再次,须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监督体系和制度,使法官受到独立的大众媒介和职业道德至上评价体系的监督。
我国目前尚不完全具备目的解释存在的实践基础。首先,法官的人格和素质是法律目的解释客观性和实质正义的最终保证,我国法官受过正式法学训练的比例比较少,法官作为一个整体的素养还不高,目前我国法官教育与法官资格制度,普遍提高法官素质。其次,目前的审判制度有待于科学化,尤其判决仅仅做三段论的简单的逻辑推理而不载明价值判断或做法理说明,这对于目的解释方法来说是最重要的实践障碍。在判决书中说明判决理由,有利于防止法官任意解释法律 。
总之,在我国目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当中运用目的性解释方法进行审判解释的实践基础并不完全具备。但是,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或法意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明显的不合常理时,如果是实践中发生较多的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社会公正作出有权司法解释,以保证司法的统一和公正。如果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个别案件,则可根据目的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作出判决,但应分析说明判决作出的理由。
第七章 刑法适用解释创造性的限度 第一节 类推解释、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概念
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存在理解上的不同。
其一是认为“扩张解释是超越了法律条文在语言学上的意义范围的解释”,国家的禁令、命令、内容等是通过法条文在语言学上的意思传达给一般国民的,那么超越语言学意义范围的扩张解释是超越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法的适用,由此产生了不应允许扩张解释的观点 。
其二是认为扩张解释是在法律条文、规范的解释中,比该条文、规范字面原意所应表明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例如将放火罪中的“烧毁”理解为只要所起的火,离开火种(引柴)能独立燃烧,不一定要将东西烧掉原形式、性质或失掉其使用价值的程度 。可见,这种扩张解释是超出字面原意,而在语义学意义范围内的解释。
其三是认为类推解释是超出刑法条文原来普通语言意思的界限,运用类推的方法作出的解释。所谓类推的方法,是“罗马法系在法的解释上的一种做法,即允许把制定法规定扩大适用于下列情形:尽管该规定措辞的最宽泛的含义亦无法包括这些情形,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属于该法规所构想的原则或社会目的的范围之内 。”
其四认为通说所说的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仅仅存在对同一事物以不同的观点来把握的表达上的差异而已,并无实质的区别。据此有类推允许说,但亦承认类推解释有一定的界限 。
仔细分析上述四种观点,可见它们只存在概念运用上的差别,而不存在内容上的实质差异。通说是第二、三种观点,即扩张解释是在法律用语的字面原意之外和其可能的意义范围内之内的解释,类推解释是超了法律用语可能的意义范围之外的解释。依此概念,上述第一种所谓扩张解释实际是类推解释,第四种之所谓类推解释实际是扩张解释。通说的观点是可取的,亦符合我国学者的一般语言习惯。下述亦在此概念意义上论述。
至于类推解释与类推适用,我国有学者对此加以区分。一般认为类推适用是法律对没有规定的行为,适用关于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来加以处罚,而类推解释是超了法律用语可能的意义范围之外的解释。但是实际上,两者只有形式的区别而没有实质的区别,“适用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应该理解为就是对“该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进行超出起其可能意义范围的解释。
第二节 类推解释之禁止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思想基础是针对国家权力而强调保护国民权利的近代思想, 。根据这种思想,罪行法定主义原则有两项基本原则:由国民代表决定对何种行为科刑和科以何种刑的“自律原则”,另一项是“预测可能性原则” 。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容之一就是“禁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是对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适用关于具有类似性质的行为的法律来加以处罚。类推适用不是根据正当程序的法的创造,违反了权利分立的原则,违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和,混淆了法与道德的区别,丧失个人利益的保障,易招致国家权利的肆意行使和对国民自由的不当压制,是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践踏,与法治国家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为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所不允许。
类推适用与罪刑法定主义的相互排斥是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的。类推适用意味着法律解释要针对客观现实的需要,立足于保护社会的价值。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立足于个人自由保障的刑法法制价值。这样,保护社会与保障个人自由在不违反被告利益,即在有利于被告的类推上就可以调和起来。因此,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虽然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但是并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例如,在阻却违法事由的紧急避险实践中所列举的……财产、自由一项,应将贞操、名誉理解理解在这一规范之内。据此,就将为保护他人或自己的贞操或名誉情况下的紧急行为,当然理解为紧急避险,视为阻却事由的存在。这就是属于有利于被告情况下的类推适用,应被容许 。
第三节 扩张解释的合理界限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是并不禁止扩张解释(通说意义上的概念),这是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观点。即使是类推允许说和不应允许类推解释的观点,如上所述,也只是概念使用上的差别,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类推解释是超出了法律条文可能包含的语言学意义范围的解释,而扩张解释是在这一范围内的解释。据此,扩张解释的合理界限就是不能超出法律条文所可能包含的语言意义范围。但是,问题并不就此解决。因为法律条文所可能包含语言意义范围本身是并不明确的。
对此,西原春夫认为,关于扩张解释的合理限度,划分的基准不是国家维持治安的必要性,而应求诸于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划分的基准应限定在以下场合:一般人会认为“如果那个行为按照这项条文加以处罚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按照同样的条文加以处罚是理所当然的 ”。
而且,刑法上的类推与其说是一种法解释,不如说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类推并不是对某个词句进行解释,看某种行为包不包括在此解释内,而是从国家社会全体的立场看某一行为的不可允许,然后在找出类似的法条以资使用,这是类推采用的思想。相反,扩张解释完全是从能否纳入法律条文解释的范围出发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 。
上述观点分别从解释结论和解释的思维过程两个方面对扩张解释的界限及其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笔者完全赞同。下面笔者拟就几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
(一)鲤鱼流出案:被告把水闸门打开,让养殖在鱼池中他人所有的大约二千尾鲤鱼流走。
(二)饮食器便尿案:被告在供顾客食用的斟酒器和铁锅里小便。
(三)挂轴污损案:供聚会等一时出租的和式房间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画着虾和鲤鱼的挂轴,被告在上面用墨大写“不吉”二字。
分析:日本刑法261条规定了器物损坏罪,其中有以下文字:“损坏或伤害前三条记载以外的物者……”对于案一,日本大审院做了该行为符合本罪中“伤害”要件的判断。对此,学者批判道:那些鲤鱼在流出后当即死亡是另一回事,如果它们在某个地方仍然生存,把这种情况看做符合本罪中“伤害”要件,从词句上看与一般人持有的标准相距也太远了。对于案二,大审院认为,这一行为事实上或者感情上已使这些饮食器处于不能象原来的目的上再供使用的状态,因而符合起器物损坏的要件。对于案三,大审院认为,这幅挂轴在价值上的受损已经达到了无法再次使用的程度,因而判定该行为构成器物损坏罪 。
从以上三个案件及其判决理由分析,笔者尝试着总结出进行扩张解释的某些规律:
首先,确立该待解释的法律词语概念的一般观念形象。具体在上例中,伤害动物(鱼)的一般观念形象应该是损害动物(鱼)的身体完整;损坏饮食器具的一般观念形象是将饮食器具砸毁;损坏挂轴的一般观念形象是将其撕毁。
其次、理解该待解释法律词语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伤害动物(鱼)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应该是危害该动物的生理健康或生命;损坏饮食器具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是损害其作为人们饮食工具的功能价值;损坏挂轴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是损害其供人们观赏装饰的价值。
第三、判断如果将该法律词语解释为涵括待决法律事实要素,是否与该法律词语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相一致。在上述案件中,案一中被告“将水闸门打开将鲤鱼放跑”的行为与伤害动物(鱼)的一般观念形象的本质并不一致,因为将鲤鱼放跑并一定伤害其生理健康或致其死亡。案二中被告在饮食器中便尿事实上或者感情上已使这些饮食器处于不能象原来的目的上再供使用的状态,因而与损坏饮食器一般观念形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案三被告的行为与撕毁挂轴在使挂轴价值受损上具有一致的本质。
当然,在实践操作中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在有些情况下显得比较难以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对两者区分没有意义。毕竟理论上的抽象的区分能够为实践操作提供某种指导,并且在某些典型案例中确能对两者加以区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思路,这在权力与权利紧张关系激化的场合,极有可能形成实质上的差异表现出来 ”。此外,将两者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强化了刑法解释必须有一定界限的观念,在观念上保障了罪刑法定主义的牢固地位。
注释:(略)
参 考 文 献
一、中国学者著作:
1、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刑法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宗建文:《刑法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4、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5、 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6、 董 嗥:《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部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兴良:《刑法司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11、罗树中:《刑法制约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12、梁彗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3、何鹏、甘雨沛: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 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
17、高明暄:《刑法学原理》(第一、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张明楷:《未遂犯论》,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
2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2、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3、蔡墩铭:《刑法总则论文选集》(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24、陈朴生、洪福增:《刑法总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25、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7、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
28、潘维大、刘文崎著:《英美法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年。
29、赵炳寿:《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杨春洗:《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杨敦先、张文:《刑法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3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3、赵常青:《新编刑法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林山田:《刑法通论》,兴来印刷有限公司,1986年版。
二、外国学者著作
1、 [南]卜思天.渝潘基奇:《刑罚理念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波斯纳:《法理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版。
3、 [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王泰译,载《刑事法论丛》(第3卷)。
4、 [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
5、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译,商务印书馆,第290、293页。
7、 [美]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中国政法部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9、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0、 [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1、[意]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马克思:《哲学的贫苦》,马恩选集第一卷。
三、参考论文:
1、[南]卜思天.渝潘基奇:《关于比较刑事法的若干法哲学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1期。
2、梁彗星:《法解释方法论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
3、胡基《审判解释方法与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4、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兼论司法法之存在极其合理性》,载《法学》1997年第3期。
5、李志平:《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6、余宏荣:《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研究综述》,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
7、陈殿福:《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及其偏差》,人大复印资料《法学》1991年第8期。
8、 张绍谦:《浅论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载《刑法发展与司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9、陈忠林:《论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0、马克昌:《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11、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2、孙笑侠:《法解释理论体系重述》,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
13、孙笑侠:《法治、合理性及其代价》,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1期。
14、吴德星:《论法治的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载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2期。
15、尹伊君、陈金钊:《司法解释论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16、张明楷:《论修改刑法应该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7、《法律解释:学理、规则与制度——“法律解释(学)”研讨会综述》,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18、余宏荣:《我国刑法适用中的司法解释》,载《刑事法专论》,第591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
19、王平:《论我国刑法解释的有效性》,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2期。
20、冯惠敏、冯军:《两大法系刑法判例法渊地位与拘束力之比较》,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3期。
21、储槐植、梁根林:《论刑法典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22、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23、钟在根等:《罪刑法定主义与刑事自由裁量权》,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24、郑强:《关于哈特的法律思想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25、刘星:《描述性法律概念与解释性法律概念——哈特与德沃金的法律概念之争》,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4期。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6
法律的存在天然与解释分不开,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离不开解释。实践中,我们很难以想象会有脱离解释的法律。因此,法律解释在法律的创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其都离不开法律解释;一般来说,在国内法中,较多称之为法律解释;而在国际法中,在很多情况下称其为条约解释。不论是法律解释还是条约解释,在解释之中难免会带有解释者的偏好--即解释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所遵循的解释规则。因此,对于采用何种规则对法律/条约予以解释,实践和理论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见仁见智。
在wto争端解决中,同样会遇到对其涵盖协定的解释,纵观其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发现,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⑴对wto各协定的条款做出了许多颇具创造性的解释,总体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⑵然而,在解释的过程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应持何种解释规则为学者们所关注,其中有不少学者担心其会走向解释的能动主义。对此,笔者以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其采用较多的仍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条约解释所坚持的客观解释规则,同时也会折衷采纳目的和宗旨解释。因此,客观解释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客观解释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运用
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客观解释规则主要是规定在"解释之通则"的第31条之中。具体对该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该条对条约解释应遵循的一般规则有:善意解释原则、约文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嗣后实践解释方法和目的与宗旨解释方法。笔者认为,约文解释方法和体系解释方法直接体现了客观解释学派的观点,从而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也是dsb对协定解释的首选,从而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根本出发点。
(一)约文解释方法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出发点与中心环节
条约解释的出发点与中心环节就是审查与阐释条约的约文。⑶因为探求条约文本的文义是条约解释的首要目的,条约的解释目的主要是阐释现存有效的条约文本的字面含义,以寻求妥当的结论,而并非探究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律。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约文解释也不例外,纵观其历史及其运行的具体实践,无论是以前的专家组还是现在的专家组以及上诉机构都特别强调约文解释的基础地位。归纳起来,在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对于约文解释方法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强调约文用语中通常含义。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报告中都强调首先要从约文的普通含义出发。对此,有学者认为,自从国际上出现wto之后,设在日内瓦的上诉机构强调以文字取义为先,和尽在咫尺设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主张的目的论(teleology),形成鲜明对照。⑷
例如,日本含酒精饮料税收案⑸是wto上诉机构审理的第二个案件,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根据国际法院的几桩判例⑹最后得出结论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的文字奠定了解释方法的基础。解释必须基于条约的约文。要按其上下文给条约规定以正常含义。在认定其规定的正常含义时还要重视条约的目的与宗旨。"⑺这段话在强调以约文的普通含义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对《公约》第31.1条的解释也十分全面与详细。⑻
第二,参照字典并重视用语的字典含义。wto成立以来,上诉机构几乎在每一起案件中都引用《牛津英语词典》作为解释wto规则的首选。⑼为了适用约文解释方法的需要,在wto秘书处以及法律司,摆设了很多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权威字典。仅英文字典就有oxford、webster、black law dictionary等版本,应有尽有。甚至有学者调侃道,查字典成了家常便饭。有些批评者讥讽地或者戏谑地说:"牛津字典(用得最多)变成了wto的一个涵盖协定。"⑽
第三,适时考虑约文用语中的特殊含义。正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4条的规定,如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应使条约用语具有特殊意义。可见,如果要采用某一术语的特殊含义的话,并不是随意的,一般需要有相关当事国有特别"确定"的指向。在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也是如此,对于一些协定中用语的特殊含义,wto争端解决机构也会赋予其该特殊的含义,当然这些也会结合缔约方所使用的协定术语本身隐含着该特殊的含义。例如,当涉及到农产品协定第5.1(b)条中"进口到岸价格"(the c.i.f import price)的含义时,由于cif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因此,在欧共体影响家禽类产品进口的措施案⑾中,上诉机构就采用了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cif的界定来解释这一用语。⑿
(二)体系解释方法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有力支持
与国内的法律解释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一样,wto争端解决机制运用上下文之体系解释方法解释协定术语含义的实践是十分普遍并且广泛的,当wto协定中词语的含义出现较多时,wto争端解决机构重视通过上下文来确定该用语的确切含义。如前文所述,就wto协定而言,这里的上下文不仅包括该用语所在的协议,还包含其他协议的具体条文。当dsb解释某一特定协定时,wto相关协定之间由于其内在联系可以被交叉引用,当然,这种引用还需要考虑不同条款之间联系的紧密型。
例如,在1995年美国棉织和人造纤维内衣进口限制案⒀中,针对美国对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产品追溯性地适用了过渡保障措施时,专家组指出:"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此未作出规定,我们应检视gatt1994的有关条款是如何处理的,后者和《纺织品和服装协定》一样都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gatt1994第10.2条就是这种相关条款。"⒁但是上诉机构对此并不赞同,其认为,《纺织品和服装协定》第6.10条己经做出相应规定。⒂由此,也许可以推导出:"在同一子协定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参考其他子协定中的同类规范。"
整体来看,wto的约文、序言与附件是争端解决机构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运用体系解释方法所依据的主体部分。约文、序言与附件包括了整个wto法律体系。在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对wto争端解决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 首先就是将意义不明确的条款或语句放入其所在的段落、篇章乃至整个wto协定中去加以解释。
综上,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几乎会在每个案例中都会运用上述客观解释规则。如前所述,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运用例如目的与宗旨的解释方法以及甚至会进行司法造法的情形,但是客观解释规则在很长时间扔会是它对协定解释的基石。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因素。
三、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客观解释规则的成因
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所具体采用的解释规则对争端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不断发展与增加,由于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建立的目的、宗旨、性质、管辖权、受案范围的不同,从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条约或协定进行解释时,会选择不同的解释规则。wto争端解决机构已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特点,而在这些特点背后,也有其自身理由及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dsb在管辖权上的强制性是其选择条约解释规则的根据。
管辖权是任何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争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受理和审理案件的依据和前提条件。具体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而言,笔者认为,wto协定在管辖权上的具体规定为其选择适当的条约解释规则解决各成员方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wto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主要在《wto协定》附件2的dsu之中。专家组在实践中参考了国际法院的审案原则以及关于国际法院内部运行的理论或学说,确认自己有权决定是否对争端有实质管辖权;这种自裁权在实践中也基本得到了上诉机构的肯定。⒃
因此,专家组断案中确定和行使自裁管辖权,即是发挥专家组审案能动性弥补成文规定不足的例证,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wto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⒄第一,专家组借助自裁管辖权,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需要,将一些附带非wto涵盖协议明确的问题纳入发表建议范围;同时专家小组可以利用司法经济原则"避免对有关wto法内部冲突问题作出明确结论"。⒅第二,专家组可以依据"管辖权之管辖权"原则,审查在更广范围内涉及非wto诉请。wto专家组有权决定听取和决定这一主张,尽管争端大部分包括国际法的其他原则。⒆专家组有权判定自己是否可以聆听有关附带wto法方面的主张,判断此方权利存在的形态,而且开始时并不需要当事方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第三,专家组在以往案例中审查了投诉方诉讼请求中的有关双边条约,比如在"巴西向欧盟出口家禽制品案"的争端解决中,巴西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中提到与欧共体的双边协议,并称欧共体违反了该双边协议,但协议本身是否属于专家组的权限范围是一个问题,因为该协议不是dsu意义上的相关协议。专家组将该问题作为实质审查前的基础性问题来解决并决定在涉及欧共体在wto协定下对巴西的义务的范围内审查油籽协议。⒇
其次,dsb的准司法性质是其坚持约文解释方法的出发点。
应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极富创意和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尽管其在诸多方面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但是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其是一个具有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构,还不是绝对的司法机制,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也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来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而作为准司法机构,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进行解释时,为了保证其权威性以及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其首选的解释规则就是约文解释规则,尊重条约约文的规定。进而去寻找相关的上下文以及嗣后相关的行为和做法。
当然,对wto协定条款的解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套用的公式,但是有一定是肯定的,即在解释的过程中,需要维持协定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和动态发展等,同时更要平衡各成员方之间的利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解释要素和规则也没有一定的位阶。但事实上,坚持善意的原则,约文解释为出发点,即以条约用语通常含义为起点,从特定的含义到上下文再到目的和宗旨,一旦约文解释仍不明或造成显然荒谬时,在考虑从所采用的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与缔结情况在内的补充解释资料中进一步寻找证据,这无疑构dsb对协定解释的基本逻辑顺序。由此,对于具有"准司法性质"的wto争端解决机构来讲,其坚守客观解释学派,更加青睐于上下文中的约文解释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wto协定"一揽子协议谈判方式"以及其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大是dsb采用上下文解释方法的主要依据。
wto以"一揽子协定谈判方式",即以其"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套餐方式适用于wto的领域,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之一。纯粹从程序角度来看,它似乎只是一种立法方式。对于,"一揽子协定"谈判方式本身,虽然在实质上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获利益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趋强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依然会在相当时间内在国际贸易立法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wto争端解决的过程中,面对wto协定的错综复杂以及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现实,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其协定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各个协定之间的交错与交叉的关系,并且较多地运用各个协定作为解释"上下文"去确定协定中的"歧义"或空白中的含义,从而以平衡各成员方在wto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
四、结语
综上,从目前wto的司法实践来看,dsb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所进行的解释以及运用的解释方法是成功、有效的,这对于解决wto成员间具体争端,澄清wto协定现有规定模糊之处,确保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及wto规则适用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前文的分析与论证我们知道,总体上,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协定解释的实践中,其对协定的解释也遵循着《维也纳条约法》的条约解释的规则:即尽可能坚持上下文中的约文解释之客观解释规则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其协定解释的主要特点。
参考文献:
⑴dsu第3.2条规定:"wto争端解决体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各成员在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bs的建议和裁决 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⑵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1页。
⑶陈欣:《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司法克制主义vs.司法能动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⑷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⑸japan - 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 wt/ds10, wt/ds11, requested on 21st june and 7th july 1995.
⑹主要是指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之间领土争端(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和1995年卡塔尔与巴林海上划界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⑺see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p. 7, adopted on 1st november 1996.
⑻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⑼陈欣:《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司法克制主义vs. 司法能动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⑽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⑾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ation of certain poultry products, wt/ds69, requested on 24th february 1997.
⑿wt/ds69/ab/r, p.51, footnote 89, adopted on 23rd july 1998.
⒀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cotton and man-made fibre underwear, wt/ds24, requested on 22nd december 1995.
⒁see wt/ds24/r, p. 7.64, adopted on 25th february 1997.
⒂see wt/ds24/ab/r, p. 12, adopted on 25th february 1997.
⒃在1916年美国反倾销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上诉机构注意到一国际法庭有权主动地审查有关管辖权问题,并使自己相信对目前进入程序的任何一宗案件享有管辖权。在此上诉机构报告的脚注中列举了大量论据,包括国际法院案例法官的意见和个别法官的意见、著名国际法学者的论著、国际仲裁规则和实践等,以此作为专家组类似地享有此种权力的论据。see wt/ds162/ab/r, wt/ds136/ab/r, footnote30,p.17.
⒄赵秀丽:"世贸组织专家小组'自裁管辖权'初探"载http://cacs.gov.cn/cacs/lilun/lilunshow.aspx?articleid=36272,2012年8月5日访问。
⒅余敏友、陈喜峰:"论解决wto法内部冲突的司法解释原则(下)"载入《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 页。
⒆joost pauwely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ajil)2001, vol95, no.3, p556.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7
宪法条文、规范、原则、结构、功能及相关的法律关系其法律含义如何揭示出来,这是宪法解释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宪法解释对象宪法本身的层次性,宪法条文和宪法规范、原则以及宪法结构和功能和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揭示手段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宪法条文含义通过语言学上的方法就能比较容易使条文中名词术语的内涵清晰,而宪法规范、原则、结构、功能及相关法律关系的含义就不能依靠单纯的语言学手段,而要借助于逻辑手段以及各种社会学分析方法。就宪法解释制度中涉及到的解释方法而言,德国学者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指出,自萨维尼以来,有四种一般的释义手段,即文理的或语言学的解释;论理的或体系的解释;主观的或历史的解释;客观的或目的论的解释。(60)日本学者伊藤正己认为,就法律解释的可取方法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61)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宪法解释方法涉及到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类推解释。(62)台湾学者左潞生从宪法解释的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于或者说为宪法解释实践所采用的几种常用的解释方法,主要包括统一解释、补充解释、条理解释和扩大解释。①统一解释,即由于宪法条文见解的歧异,而统一确定其意义,此项方法可明确某项宪法条文的语言含义,指明条文的适用范围,以使全体人民一体遵从。如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所谓“溯及法”(expost facto law),其义曾发生歧见,经1789年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确认溯及法包括四种法律:对行为时无罪的行为,事后加以刑罚的法律;事后加重刑罚之法律;事后变更刑罚的方式,使犯人受较重刑罚的法律;要使犯人陷入于罪而事后变更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自此对该条规定的误解消失,全体人民得以有效遵循。②补充解释,即由于宪法条文规定的疏漏,予以适当地补充其意义。这种规定可以弥补条款内容的缺失,而使宪法在实际运用中,能发挥更加灵活完整的作用。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2条规定,总统提名大使、公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及合众国政府其他官吏,应经参议院的劝告及同意加以任命,但未涉及免官问题。然而任官权与免官权有密切关系,倘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能灵活运用。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yers v. united states.1926一案判决中,承认总统行使免官权为合法,便创补充解释的先例。③条理解释,即由于宪法条文规定得简略或含混,依文义、法理、论理、先例、类推等准则,予以正确地阐明其意义。此项方法,在宪法解释实践中应用最广。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规定,“国会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人数认为必要时,得提出宪法修正案“。但所谓三分之二,究竟指议员总数?或是指法定出席人数?因文义含混,无法判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20年的national prohibition cases (253 u.s.350)案件中,对此条文予以解释,认为是指法定出席人数而言。
其理由是宪法一方面既已规定“国会各院执行职务,以议员过半数为其法定人数”(联邦宪法第1条),同时在此条文内,又无除外规定,应在逻辑上合理解释为法定人数。④扩大解释,即由于社会情况的变迁或进步,宪法上的规定不足以应付现实的需要,而予以及时扩大其义的方法。此项方法,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能免除修改手续,而赋予宪法以新的含义。例如,美国联邦宪法为刚性宪法,修改不易,制定近200年,修改仅26条,其能应付时局变迁,完全倚赖于解释,其中最为著名的如联邦宪法增修第5条至增修第14条,均明确承认自由放任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19世纪后半期,联邦最高法院又正式承认,以契约自由为联邦宪法增修第5条及第14条所谓“正当法律程序条款“(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所保障的自由权之一。直至20世纪3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仍然支持这一原则,宣告规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劳动时间的法律或统制物价及其他经济活动的法律无效。但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鉴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于是放弃往昔所指的原则,转而保护劳工权益,并支持劳工立法为合宪。由此可见,在美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宪法条文的含义是可以随着时局的变迁而作适应性地扩大,正由于这种扩大解释,使宪法避免了修改程序,维护宪法稳定性的形象。(63)
尽管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对宪法解释的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但笔者认为,学者们对宪法解释的方法的分类经常将宪法解释的原则、方法和结果混在一起,因此,常常给人们一种层次不清晰的印象。诚然,宪法解释的原则同宪法解释的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说,宪法解释的原则就是宪法解释的方法,以不同的解释原则来理解宪法就会得出不同的含义。但宪法解释的原则毕竟只是一种方法论,它不可能概括具体的宪法解释手段。宪法解释的方法应该是技术层面上的解释宪法的手段,而不是一般的方法论。宪法解释的结果同宪法解释的方法也有着密切联系,不同的解释方法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但相同的解释方法也会因解释目的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果,故宪法解释的方法同宪法解释的结果是分属两个不同哲学范畴的概念。从结果来划分宪法解释方法的类型并不很科学。
为了避免将宪法解释的原则等同于宪法解释的方法,笔者从宪法解释的实践出发,对宪法解释的方法作以下几种新的角度的分类,其旨在于更好地认识宪法解释实践中可资操作的技术手段。
1、从宪法解释的依据来看,宪法解释的方法可分为立足于宪法条文的解释、从宪法精神出发的解释、历史资料的解释、外国资料的解释、目的论解释以及制定法规则解释、其他法源解释等。
(1)立足于宪法条文的解释。立足于宪法条文的解释是宪法解释中最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宪法解释制度产生和形成的初期,字面解释原则盛行,对宪法条文含义的解释实行严格的客观主义,宪法条文中上下条款、相关条款都是解释宪法条文含义的直接法律依据。一些成文宪法还在宪法中就该宪法中涉及到的若干共同的名词术语、法律关系作统一释义附于宪法之中,以供理解宪法相关条文时用。以塞浦路斯1975年宪法为例,该宪法第186条就规定:在本宪法中,除另有明文规定或上下文另有需要者外:a、“族社”指希腊族社或土耳其族社:“法院”(庭)包括该院(庭)任何法官:“希腊族(人)”指第2条规定的希腊族社的成员:“法律”专用于本宪法生效后的时期时,指本共和国的法律:“人”包括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的公司、合伙企业、协会、社团、机构或团体:“共和国”指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人)”指第2条规定的土耳其族社的成员。b.表示阳性的词包括阴性在内,单数形式的词包括复数在内,反之也一样。c、本宪法赋予制订任何命令、规则、条例、章程、或指示的权力,应包括以类似方式行使修改或撤销该命令、规则、条例、章程或指示的权力。
(2)从宪法精神出发的解释。从宪法精神出发的解释即从宪法条文中可以明显推导出来的依据来解释宪法条文的含义。有的学者将这种解释方法又分为两类,一是宪法原则解释法,就是从宪法的原则出发来解释宪法;另一就是类推解释法,即对需要进行释义的条文比照最相类似的宪法条文的规定进行释义。在此方法上,成文宪法的规定很多。如南斯拉夫宪法序言就规定,序言中所规定的各项宪法原则是解释宪法的基础。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则规定,如果最高法院在审查法律、法规、章程、条例是否合宪时,发现联邦法规同联邦宪法精神不一致,或正在审议中的地方法规或章程的某些条文同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精神不一致,则联邦或酋长国有关当局必须采取步骤取消或修改同宪法不一致的部分。为了使宪法精神贯彻于宪法解释实践的始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永久宪法还特别规定,最高宪法法院院长和成员应在有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参加的协商议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宣誓:“我以全能的真主的名义宣誓,我将遵循古兰经的教诲和穆罕默德的教律,忠于我的宗教信仰、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保卫共和国制度和革命目标,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人民谋取自由、利益、财富和尊严,竭尽全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保卫国家安全。真主将为我的诺言作证。”
(3)历史资料的解释。历史资料的解释是历史解释派的主要观点,即当没有明确的宪法条文依据来解释宪法的含义时,应该收集和查询制定宪法时相关的历史文件,并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解释宪法可资参照的依据。历史资料解释法是在违宪司法审查解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但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逐渐遭到现时主义者的抨击,因此,以历史资料解释宪法日益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和场合。正如温尼斯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宪法解释中可能必须求助于历史资料,但仅限于为了消除含混、荒谬或其他疑难。”(64)
(4)外国资料的解释。外国资料的解释即适用或参考外国宪法的有关经验来解释本国宪法的含义,此法一般只适用于在法律传统上有密切联系的国家。英联邦国家常常采用此法来解释本国宪法的疑难。如在尼日利亚,从独立之日起,最高法院就掌握了比较宪法的资料,并愿意在宪法解释中使用它们。它经常援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北爱尔兰的判例。尼日利亚学者对此也表示赞赏。卡苏尼姆教授认为:“参考其他宪法条文无疑是明智的。”(65)在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解释宪法时也特别注重运用比较法的资料。最高法院明智地指出:“当你面临所解释的宪法条文不甚清楚或不明确的难题时,你会倾向于探询:其他国家的思想是如何回应由其他国家宪法相似规定所提出的挑战的。”(66)
(5)目的论解释。目的论解释法在法理上属历史资料解释法的一种,但目的论解释并不注重历史资料的文字规定,而是侧重于对历史资料中所提供的线索的分析来判明制定者在制定宪法条文时的真实意图,故目的论解释法又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主观历史资料法。
(6)制定法规则解释。制定法规则解释法在法理上称之为依据解释法的解释法。解释法在英文中称为interpretation act或interpretation statute.解释法在英美普通法国家比较发达。如在加拿大1967-68年就制定了《解释法》,而北爱尔兰则在1954年就制定了《解释法》。有些国家的成文宪法还明确地肯定了《解释法》在宪法解释中的法律地位。如1962年尼泊尔王国宪法第91条第2款就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依照本宪法的规定,用于解释尼泊尔法律的《尼泊尔法律(解释)法》适用于解释本宪法”。
除了上述各种依据可以用来解释宪法外,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还有一些法源可以用来理解宪法的含义,主要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确立的法律原则对下级法院的拘束以及本国有效的国际条约等。如孟加拉国宪法第152条规定:1897年“一般条例法”关于议会法令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本宪法;以议会法令使任何条例废止、无效后失效。巴基斯坦宪法第201条也规定:除遵守第189条的规定外,最高法院有关法律问题或解释法律原则的任何决定,对所有下级法院有拘束力。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则规定:解释本宪法含义模糊的文辞,解释时应对1952年2月11日苏黎士协议和1959年2月19日伦敦协议的文字与精神给予充分的注意。
2、从宪法解释揭示文义的手段来看,宪法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定义法、扩张法、缩小法、准据法等。
(1)定义法。定义法是宪法解释中最常用的解释手段。reed dickerson认为,立法上“定义”分为三种:①名称性定义,是对一种不常见的词句,以比较通俗的语句去表示它的意义。如“称折裂者即指破裂”。②内涵性定义,是一种最主要的定义。如称“化妆品”者,指“以洁净或美化身体或变更颜面之物品”。③外延性定义,是对含义较广的词句,用列举方式表示这个词句所伸延的范围,如“麻醉剂者”,指“鸦片、古柯叶、古柯碱、鸦片制剂或其他由上述物质所产生之碱,或用以制成上述物质的原料”。(67)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定义法持谨慎态度,如richard robinson在《定义论》(definition)一书中指出,规定定义的最高原则便是尽可能少地作规定。他认为,“毫无疑问,一个法规可能包括定义-其常常附带产生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更多。”(68)尽管关于定义的功能有许多法理上的争论,但定义法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的应用却是普遍的,尤其是成文宪法国家运用定义法来进行立宪解释构成宪法解释的一大特色。以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91条的定义法为例,其定义法涉及到了名称性定义、内涵性定义和外延性定义三个方面。如该条规定,“政府”(government)这一名称的含义是指“新加坡政府”:“选举人名册”(register of electors)的内涵为“根据有关选举的现行有效成文法律规定所制定的选举人名册”;而“成文法律”(written law)的外延则包括“本宪法和马来西亚宪法以及所有在新加坡内现行有效的法令、条例和补充立法,并包括根据1958年新加坡(宪法)敕令所制定的规则、规程,只要它们在新加坡仍系有效者。“
(2)扩张法。扩张法指解释宪法条文含义时,尤其是要揭示由宪法条文所表达的宪法规范、原则的含义或者是结构、功能及相关法律关系的特点时,基于一定的解释标准,对宪法条文规定的含义作广于字面规定含义的理解。扩张解释依台湾学者杨仁寿之见,它同目的论解释有所区别,且异处在端视是否在文义“预测可能性”之内。如依照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的“射程”理论,在文义射程之内者,为扩张解释。如所扩张的文义,非原有文义所能预测,超出射程之外,则不能为扩张解释,仅能为目的论扩张。换言之,扩张前后文字内涵相同,应为扩张解释;文义内涵不同者,不能为扩张解释,如有贯彻规范意旨之必要,则应为目的论扩张。(69)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扩张解释法源于美国违宪司法审查解释情势变迁理论,并以最高法院关于“正当程序”的解释为显要释例。该条款载于宪法修正案第14条:“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最高法院在19世纪中叶以前,通常把它解释成为“正当的司法程序”,也就是说所谓的“普通法程序”,指在民、刑事案件的审判中,给予原、被告以合理的程序保障。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对“正当程序”的解释就不仅指司法程序,而且扩大到包括“立法程序”,甚至包括“立法动机”。其理由出于:如果立法的内容不符合宪法的精神,那么立法也就不符合“正当程序”,因此,必须进一步追究“立法动机”。
(3)缩小法。缩小法指对宪法条文中过于广泛的含义作符合宪法规范特点的限制,当然这种缩小必须是具有合宪目的的缩小。从宪法解释的实践来看,定义法基本上都是缩小宪法条文字面的文义,而对宪法条文的内容作内涵和外延上的界定,如前述所指新加坡宪法将“政府”释义为“新加坡政府”,这就是将“政府”一词作缩小解释的范例。
(4)准据法。准据法也是宪法解释中的一项释义技术,与上述几种方法不同的是,准据法并不直接释义,而是指出理解某个宪法条文规定含义的可以参照的准用性规范,故准据法是一种间接释义法。如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第82条就规定,本宪法附件三开列的本宪法条款采自1959年2月11日苏黎士协定,是本宪法的基本条款,不得以删改、增补、或废止等任何方式予以修改。准据法在宪法解释实践中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准用性法规为外国资料时,受到的批评就更多。如尼日利亚最高法院法官韦斯康特。拉德克利菲1963年为英国枢密院写道:虽然西尼日利亚宪法体现了联合王国宪法的某些原则和惯例,但不应认为这类原则和惯例在宪法解释中对尼日利亚的法官具有拘束力。(70)
3、从宪法解释结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宪法解释的方法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在立宪解释中,宪法解释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条文自释、条文互释、专条释义和专章专节释义;在行宪解释中,宪法解释的表现形式一般较随意,解释的内容可以表现在行宪文件中,也可以表现在行宪活动过程中的言论、传媒之中;在违宪司法审查解释和监督解释中,宪法解释可以表现在司法判决文书中,也可以表现在专门监督机构的裁定文书之中。现仅就立宪解释中的释义表现形式作简单分析。
(1)条文自释。在立宪解释中,条文自释可以说是宪法解释的最直接的手法。
从立宪技术的角度来看,条文自释又是宪法条文中宪法规范、原则构造的基本技术之一,故有些学者把条文自释看成是立宪的技术手段,而不视为释宪手段,只有以专门的释宪形式存在的释宪条文才为释宪。从成文宪法的规定来看,几乎每一个宪法条文的规定都是一种条文自释,这种自释的对象就是界定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条文自释中常采用的方法是定义法、客观描述法、逻辑假定法、逻辑规定法等。定义法就是宪法条文对某个名词术语进行定义,从而对宪法所要调整的这一社会现象的含义予以揭示。以1937年爱尔兰宪法为例,该宪法第4条规定:国名叫做“爱尔”(eire),或按英语称为“爱尔兰”(ireland)。第5条规定,爱尔兰是一个主权、独立、民主的国家。上述两条规定就是通过定义法来确定宪法所规定的某个名词术语的内涵。客观描述法指宪法条文将某种调整对象的客观特征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以利于对宪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如爱尔兰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领土包括爱尔兰全岛、其他岛屿以及领海。逻辑假定法是从某个学说、理论前提出发,来确定某个宪法调整对象的性质,其假定法多出自于逻辑上的主观假设,此种释义法构成了宪法的主观性特征。如爱尔兰宪法序言就规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为一切权力的来源。逻辑规定法是构造宪法规范的基本手法,它将行为条件、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以示人们遵循。宪法规范就其哲学特征而言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相结合。就其客观性来说,规范内容的设立来自于实践中相同行为经验的总结;就其主观性来说,规范内容并不是实践中相同行为经验的简单反映,而是带有一定宪法程序要求的行为。如1953年丹麦王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王任免首相和大臣。国王决定大臣的数目及其职务分工。第16条规定国王或者议会对失职的首相和大臣可以提出弹劾。上述对国王权限的规定是在“可以”行为模式下对某种行为发生可能性的肯定,它必须是依法的行为,同国王随意作出上述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为宪法行为,而后者则是普通行为。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8
关键词:罪刑法;刑法解释;原则
在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刑法修订也建立了相对应的刑事立法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的建立,适当的推动了我国刑事范围内法律制度化的进程。但是因为刑法解释具有很强的任务性和实践性,自从我国开始推行刑法解释之后,相应的罪刑法定原则对其也有一定的制约和限制。本文主要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限制因素进行研究,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表现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限制效用,帮助我国建立更加全面的立法制度。
1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
在刑法系统中,罪刑法定原则是所有原则中最为主要的原则之一,所以,不论是司法系统还是刑事立法的有关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效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刑法解释中它的作用也是非同小可。通常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都以获得人权自由为最主要目标,最大化的实现在同一时间内对司法和立法权的制约,它也在不断的寻找两者之间的融合点,相应的刑法解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范围。
刑法解释是解释范围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和其他的解释进行比较,它还具有其独到之处,即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上,它的侧重点是解释不能超过刑法自身和所拥有的解释性效用。所以,在司法实行的过程中,法官要站在法律的角度,构建解释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因此也可能出现很多种解释模式,相应的解释结果也是多种多样。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要进行恰当的选择,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前期准备工作,例如劝说力、和现在的法定标准相吻合等。[1]法官的选择不是进行历史性的检验,而是根据现在的法律状况进行相应的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法官在进行解释的时候,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对解释进行随意筛选,它所进行的选择要符合高水准和高质量的标准。
2 刑法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联系
作为刑法体系当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无论是刑法解释还是罪刑法定原则,二者在同一目标、总体目标与基础等方面的实现途径还不尽相同,也就是说表现为一定的矛盾性。虽然有一定矛盾性存在,但二者还是可以相互协调与转化,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也正因为如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具有一体化的法律价值基础。司法实践是法律顺利实行的重要保障。换句话说,实体正义也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司法和立法之间存在相应的互动效应。并且,立法和司法实际上也不是不相容,两者在相互修补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司法解释的进程。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能够有效的保护人们的实际权利不受侵害,限制一部分的国家权利。在法律模式中,它是保护人权的关键和基础。通常情况下,该权力的实行要和社会的实际相互融合,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状况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在改进的时候还要融入相关的法律解释。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把该原则中的内容作为社会调整和改进的重要标准,如果在相同的刑法解释中出现了重复的情况,就可以以此为依据进行恰当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相互融合是完成社会实践和基本条件的关键。[2]
3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限制
(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要求优先文理解释
首先,在罪刑法定原则中,其刑法解释的原则一定要严谨。因为刑法和人们的生命联系紧密,所以保持严谨的态度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素之一。其中严格解释原则就是指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规定进行说明的时候,不论是哪种行为都不能受到惩罚。换句话说,即使出现类似的状况,但是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就不能进行惩罚。所以,只有对刑事法律进行严谨的解释,才可以更好的处理刑事法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公正状况。在这里所强调的严格解释,实则是应当严格对被告人不利的相关解释的限制,同时,对被告人产生有利的解释行为则不适应此条款。针对“不利于”条件的规定以及相同法律,从目前各国的刑法体系上来看,基本上都是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当地民众认可度以及不同刑事政策地而启用的不同处理之法。[3]
再者,严格解释的限定使得文理解释成为首选。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比较注重的是,人们只能认可之前公布的相关法律,并对其进行统治。通过这种方式,依照字面意思进行相关的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实际的法律解释范围中的实际化要求。所以不论哪种模式的法律解释,都要使用相关的语言分析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理解释法。在法律范围中,假如我们能够把其他的解释和文理解释融合起来,两者保持其统一性,那么法律的约束性也就不存在了。[4]正是这样,法律条文的实际意义就是众多的解释者要首先被计入考虑的范围之中,如果出现了含义模糊不清,就可以把相关的解释计入考虑的范围之中,所以文理解释和其他类型的解释进行比较,具有其显著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也并不是绝对的,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也具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在融入文理解释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不相适应的结论;可能出现不相同的结论;在法律条文中只有一种含义并且意思清楚明了的状况下,但是结果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状况,就可以引入其他的解释方法;法律出现的时候,不能在法律条文中找到相关的结论时,也属于这种情况。[5]
(二)在罪刑法定原则中,增加解释的制约性
所有的事物都要受到有关事物的制约,增加解释也是如此,它不能无止尽的把自身的含义进行扩张。增加解释自身的限制主要是什么?如何合理的处理这个问题呢?针对这个问题,我收集了中外刑法界中相关的几种观念,并且进行研究。首先,刑法条文中最广泛的可能性观点。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增加解释可以以射程、文义为主要限定,如果其中的实际含义超过了射程,就不能把其结果归结到适当的解释范围之中;并且还会超过我国刑法中的实际含义,但是站在实践的角度,就不能超过我国刑法中所限定的可能性含义。再者就是逻辑含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中,这种观点,不论是使用哪种解释,其基础都要在法律条文的基础上符合实际的逻辑含义来进行,可以根据需要解释的用语和条例以及需要进行解释的对象都要在被包含和包含的范围中来判断法律逻辑语义的实行范围。[6]还有,人们预测的可能性。西原春认为,增加解释的划分界限就在于人们预测的可能性。在该观念中,如果把保护国家安全作为评价解释的基本,就容易让人们失去自由。我个人比较赞同把人们预测可能性和刑法条文最宽含义的可能性说进行有效的融合,相关的观念都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对前一学说的实际化过程。其中对最宽含义的可能性的确定,可以以哈特的观念为基础,他认为,不论是哪种词语,都具有两个部分的含义,边缘化含义和主要含义,主要含义是确定的,但是边缘化含义却没有清楚明显的划分。但是和很多种解释进行对比,条文的通俗意义还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中,怎样有效的把握词语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人们预测的可能性和词语最广泛含义相融合。
扩张解释是我国进行自主载量权的主要部分,并且被普遍运用到现在我国内外刑事活动中去,并且和有关的罪刑法相吻合,其主要根源就是在于自身的制约机制,它们敢于和传统的法定原则进行挑战,进行改进,还和法律法规的本意相吻合,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它们能够有效的弥补罪刑法定原则中的不足,所以其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8]
4 结束语
本文在研究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以期能更好地突显出罪刑法定对刑法解释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将更多的考虑法律的实际情况,运用发展性的眼光来看待罪刑法定原则,更好的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实际利益。
参考文献
[1]沈玮玮,赵晓耕.家国视野下的唐律亲亲原则与当代刑法——从虐待罪切入[j].当代法学,2011,26(3):36-43
[2]米铁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考量[j].学术交流,2012,(6):40-43
[3]沈子华.青少年犯罪的“激情”与基本权利保护——从“药家鑫杀人案”到“少女毁容案”[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3):462-468
[4]杨琼.再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读贝卡里亚的《犯罪与刑罚》,[j],法制与社会,2010年18期.
[5]毛舒逸.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j],长春大学学报,2011年05期.
[6]梁云宝.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0年11期.
[7]杨兴培.检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前中国的命运境遇———兼论中国刑法理论的危机到来,[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01期.
[8]王昭振.刑法解释立场之疑问:知识谱系及其法治局限———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初步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05期.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9
〖关键词〗经营判断原则 董事注意义务 责任 关系
经营判断原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1]是美国司法上针对股东就董事决策的失误或判断错误而提起诉讼时,法院立案和审判时法官所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这一概念的涵义,尽管人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其中心内容就是指董事的经营决策只要是出于善意、并且以尽合理的注意,董事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换言之,股东不得仅仅因为董事们的经营决策失误而主张损害赔偿或主张董事的决策无效。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的关系在美国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而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发表过不少意见,争议也很大。但总的来讲,有的学者是从义务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则从责任的角度发表了意见,但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认识。本文拟对此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一、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
在美国,学者之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董事经营判断原则实际上是董事过失责任的免除手段,此为pennington教授所主张。根据pennington教授的观点,当董事被他人提起诉讼时,董事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庭免除他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法庭认为董事在行为时是诚实的、合理的,并且如果法庭认为董事在行为,根据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董事所承担的过错责任是应当公平地加以免除的,则法庭可以根据自己认为公平的条件免除董事的法律责任。与pennington教授主张一致,《不莱克法词典》认为“它(经营判断原则)是指豁免管理者在公司业务方面的责任的一个规则,其前提是该业务属于公司权力和管理者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且有合理的根据表明该业务是以善意方式为之。”[2]既然是“免责”说明董事本身是存在过错的(这里仅指轻过失),也就是说,董事没有承担责任并不表明没有违反注意义务,只不过这种违反义务的情形依法理应当免除其责任。在这里,义务和责任不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即表明董事没有违反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因此,董事的行为即便造成公司损害,也不能构成过失。此观点为clark教授所主张,根据这一观点,除非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基于过失作做出的,或者是基于欺诈、利益冲突或非法性而做出的,否则董事的经营判断是不能被提起起诉和加以攻击的。“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假定,董事在做出某一经营判断时已经对公司事务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3]也就是说,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存在一致性。
在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免责说(或补充说),即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对董事注意义务的重要补充。这是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如刘俊海认为“经营判断原则应当被视为对董事善管义务的重要补充,具体说来,在董事会作为合议体进行经营判断时,尽管各个参与决策的董事的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他们可以主张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在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依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行使经营判断决策权时亦应作同一解释。但是,如果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董事的经营判断存有重大过失则不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4]徐晓松也认为“这一原则(指经营判断原则)现已经在美国各州被普遍承认,成为董事勤勉、注意和技能义务的重要补充。”[5]此外,曹顺明博士也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对董事注意义务在经营判断方面的另一种表述,它更为明确地划定了司法在审查董事经营判断方面的界域。”认为“经营断规则是一种限制董事责任的法理。它的效用在于,当董事因经营判断失误而受到追究时,董事可据以主张符合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免责。”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公司法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使董事的经营判断行为存在被认为违反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但只要这—行为符合经营判断原则的要件,则排除了对董事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从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司法审查。故经营判断原则的存在是以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为前提的。” [6]可见,免责说(补充说)是与pennington教授主张一致的。
另一种是无过错说,认为“除非董事在做出决议时有过错,否则,他们所做出的经营判断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认为,董事在做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时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因此,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无过错的董事行为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行为。”[7]即认为,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注意义务之间存在一致性,董事经营行为适用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即表明董事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尽管这种行为的结果最后被证明是一种失误判断并给公司带来损失,董事也不负赔偿责任。该学说与clark教授主张一致。
笔者基本赞成上述“无过错说”的主张,认为“免责说(或补充说)”在理论和实际方面存在诸多疑问[8]:
1、补充说忽视了对注意义务和经营判断原则(或经营判断原理)在美国产生历史的认真考查。事实上,经营判断原则最早产生于美国,尽管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许多国家公司制度中都有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也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引进经营判断原则,但真正能够全面反映二者关系及其变化的,只能是在美国。所以,研究二者关系也只能具体地考查它们在美国的情况。从二者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在美国,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原则要比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产生时间要早,尽管二者首先都是以判例的方式出现的。据现有资料表明,在美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经营判断原则的判例是1829年路易斯安纳州最高法院判决的percy v. milla- udon案。此后,1847年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判决的godhold v. branch bank案、1850年阿里兰州最高法院判决的hodges v. new england screw co.an 案均根据经营判断原则拒绝令董事对合理的经营失误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经营判断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在普通法上出现了,而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相关判例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以判例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作为董事注意义务的成文规定的《美国示范公司法》产生的时间则更晚。英国虽然是最早在判例法上承认董事注意义务的国家,但是,一是没有资料表明该国判例法上已经承认了经营判断原则,二是董事注意义务在判例中的形成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因此,从经营判断原则与注意义务在美国产生的时间上来看,经营判断原则要比注意义务产生时间要早,产生在先的经营判断原则对后出现的注意义务显然不可能存在补充关系,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2、从内容上看,经营判断原则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实体方面的规定,即义务与责任的规定,也包括了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要求。只不过有关注意义务的内容并不具体,还十分含糊和原则而已。例如,前述特拉法州关于经营判断原则的含义中就使用了“熟悉情况”“怀有善意”“并且真诚相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不存在自决权滥用”等词语,这些实质上就是经营判断原则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要求。经营判断原则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体,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远远超出了董事注意义务这个单一的范围。因此,不可能是注意义务的补充。事实正好相反,由于经营判断原则中关于注意义务的规定十分原则,在实际操作上很困难,美国法院在判例法上对经营判断原则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成文法上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具体判断标准(学者通常所称的“董事注意义务”)就是对经营判断原则的进一步补充。这才是二者合乎逻辑的关系。
3、考查二者关系应当注意区分“善管义务”与“注意义务”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内学者在阐明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原则(或经营判断原理)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将善管义务与注意义务混用。[9]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学者一般认为,董事义务包括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两个方面。大陆法学者通常认为董事对公司负有善管义务,有的学者又将其直接称为善管注意义务,那么,善管义务与善管注意义务究竟是否是同一概念?笔者认为,尽管人们在提及董事善管义务时多强调董事注意义务,但善管义务本身并不排斥忠实义务。例如,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规定董事注意义务的同时,对受任人忠诚处理委任事务也作了规定。根据瑞士债务法第398条第2项的规定,受任人须忠实地处理委任事务。事实上,善管义务的范围应比善管注意义要大,其不仅要求委托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应尽一定的注意义务,还要求受托人忠实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在研究经营判断原则与注意义务关系时,将善管注意义务的含义扩大为善管义务,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所以,笔者认为,从经营判断原则产生的历史来考查,作为一项实体规则,经营判断原则首先表现为美国公司制度中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规则。它是从判例法的角度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原则性的规定,而董事注意义务(后来美国成文法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的规定只不过是对前述业已确立注意义务原则所作的完善和补充。
二、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责任的关系
那么,clark教授的观点以及国内的“无过错说”是否就正确反映了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无过错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二者的关系,但仍不全面。因为,他们在考查二者关系时虽然注意到了经营判断原则中的义务内容,但却忽视了其中在实体方面的责任规定。事实上,国内许多学者在研究经营判断原则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该规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研究方面,而很少研究该规则所包含的在确认董事第二性的注意义务(即违反注意义务承担的责任)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尽管经营判断原则没有从正面或直接回答董事第二性注意义务问题,但却从反面或间接的方式反映了这个问题,即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原则。
美国《修正示范公司法》第8?30条 (d)规定,当董事依照本条规定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就无需为他作为一名董事而采取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据此学者普遍认为,经营判断原则只不过是董事注意义务违反的一项特殊的免责条款。其实基于委任关系说[10],日本、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责任属于违约责任,“董事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属委任合同关系,那么,董事在执行公司委任的公司业务时就应负诚信和勤勉的义务,董事不履行对公司诚信和勤勉的义务,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董事自应负违约责任,或者叫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11]有学者还指出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可能性问题,认为董事违反其向公司所负的注意义务时,其向公司所负的责任纯系债务不履行责任;但当董事违反其向公司应负的忠实义务时,实质上是违反其与公司间委任合同,因而应当向公司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但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又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利(含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因而又应当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产生了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请求权规范竞合说的理论,在此种情况下,公司可自由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向董事或主张债务不履行责任,或主张侵权责任。[12]
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纷纷修改公司法以降低董事责任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允许章程条款取消或降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须承担的金钱赔偿。由于公司章程属于属于契约的范畴,因此,这可以说董事的注意责任具有一定的约定性。但美国限制董事注意责任主要还是通过公司法直接加以规定的,如改变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的过错标准、确定董事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都是公司法直接规定。责任的基础来源于义务,很显然,董事的注意义务并非公司章程或合同所约定,而来至于法律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违约责任论还是违约、侵权责任竞合论均不能准确定位董事对公司民事责任的性质。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种责任既非违约责任,亦非侵权责任,而是一种法定责任。[13]
义务与责任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为,他应当受到制裁。“对一定行为负责”就是一种法律义务,“他应受制裁”就是一定的责任方式。所谓的法律责任,是指“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下的不利后果。”[14]既然董事与公司间是一种法定的关系,董事义务是法定的义务,就内在地包含了责任的法定性质。[15]
那么,在董事注意责任方面的归责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经营判断原则只是以正面的方式原则性地指出了董事在完成应尽义务时不承担责任的情况,而归责原则问题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从历史上,基于鼓励人们尽心竭力地为公司提供服务的考虑,传统英美公司法认为,董事并不对任何形式的过失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而仅仅对重大的过失所导致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美国法律,一个行为人所犯下的单纯的错误并非构成过错,如果行为人在犯下此种单纯的错误时达到了一个有理性人的行为标准。董事在作出决议时,即便犯下了诚实的错误,如果此种错误是一般有理性的人均会犯下的错误的话,则董事的错误并非是过错。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关系是:除非董事在作出决议时有过错,否则,他们所作出的经营判断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换句话说,经营判断原则认为,董事在作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因此,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无过错的董事行为(即使是经营判断失误)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的行为。这一点也说明“免责说”关于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原则之间关系的解释与美国法律规定经营判断原则的宗旨存在明显不相符合情况。[16]正如lindley m.r.指出:“……虽然董事所承担的注意义务的标准很难加以说明,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董事并不对他们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承担法律责任,虽然对于这些错误而言,如果他们尽更大的注意的话,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的过失并非表现在他们没有尽一切可能的注意,此种过失必须是超过此种程度的更具有责难性的行为;它必须是就商业眼光来看是构成严重的过失或重大的过失行为。”[17]
可见,经营判断原则作为一项实体规则,在美国公司制度中除了表现为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基本规则外,还是一项关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原则,即董事并不对他们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承担法律责任,而仅仅就其经营判断在存在重大过失或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法律责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法,尤其是美国司法逐渐放弃了董事仅仅就其重大过失或严重过失承担法律责任的理论,认为任何人,只要同意担当公司职位,即要具备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作为一般原则,董事至少要对公司所从事的商事活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此,董事应对公司从事的商事活动的基本方面加以熟悉。因为董事要达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因此他们不得以自己欠缺此种一般注意义务所要求的知识作为自己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18]从责任内容来看,董事在做出引起争议的经营判断时如果已经尽了一个有理性人所承担的谨慎行为的注意义务,董事的行为是无过错的,经营判断原则仅仅保护董事的无过错行为而不保护董事的有过错行为,因此也就谈不上“免责”的问题。[19]
需要指出的是,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原则并没有明确回答董事注意责任的归责问题,而是以间接的方式,从侧面原则性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具体的规则则留给了以后的判例和成文法加以解决。长期以来普通法上形成的经营判断原则,虽然法官们把它称之为既是诉讼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又是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实体规则,但是要董事们根据浩如烟海的判例法规则行事,他们仍然会手足无措。有鉴于此,当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公司法均规定了有关董事注意义务的一般条款。《示范公司法》第8?30条之规定是这种一般条款典型代表。
总之,笔者认为,经营判断原则是一项综合性的判例法规则,从实体和程序来看,它是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统一。而从实体义务和责任来看,它即包含了对董事注意义务的原则性要求,也包含了对违反这一义务的归责原则,是义务规则与责任规则的统一。经营判断原则与董事的注意义务之间确实存在着补充关系,但在这个补充关系中,董事注意义务处于补充地位,而经营判断原则则处于被补充地位,这与目前国内学者所持的“补充说”中二者地位刚好相反。从程序规则来看,经营判断原则还包含了股东对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诉讼案件在审理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
[1] 对于“business judgment rule”这一概念,国内不同学者翻译上存在差异。有的译为“经营判断准则”(见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有的译为“经营判断原则”(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有的译为“商事判断规则”(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有的译为“业务判断规则”(见(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刘李胜译《公司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而我国台湾学者一般译为“经营判断法则”(见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笔者基于本文之观点,认为应译为“经营判断原则”较为恰当。
[2] black‘s law dictionary,p181.
[3] robert charles clark,corporate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p.124-125.
[4]见刘俊海著《份公司股东权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
[5]见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见曹顺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7]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8]学者在研究二者关系时所称的“董事注意义务”,实际上仅指后来美国判例法和成文法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规定。
[9]参见刘俊海著《股份公司股东权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
[10]关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有不同学说,学者多有研究,在此不便多述。
[11]见耀振华《公司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研究》,《法学评论》1994年第3期。
[12]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186页。
[13]见童兆洪《公司法法理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4]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15]见童兆洪《公司法法理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6]见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368页。
[17] lagunas nitrate co.v.lagunas syndicade(1899)2ch.392,435.
[18] francis v.united jersey bank 423 a.2d 814(n.j.1981)。
法律规则的含义篇10
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具体化;法律保留原则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6-0022-10
基本权利具体化是宪法原理的一个规范命题,它古老且独立,从属于宪法实施,既关乎如何实施基本权利的问题,也关乎解释宪法基本权利的问题。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涉及法律的概念、宪法与法律、立法者与宪法、基本权利与法律的关系。其实质在于,相对于宪法规范,立法者的任务何在?
然而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详细定义何为,特别是在与规范的基本权利原理相关联的意义上,中外宪法文献却鲜有论及,这使得基本权利具体化这一至为重要的概念仅停留在通俗与含混的理解上,其意涵未能获得确切的内容。在我国的学术语境与脉络中,基本权利具体化包含三方面内涵:一是宪法的规定具有原则性,缺乏普通法律的法律要件构成;二是宪法是最高法,普通法律须贯彻上位法;三是只有通过普通法律规定具体的实施要件之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才可实现。该命题无论在宪法理论还是实践中均有其合理性,但未免失之简陋。理论上,它包含了宪法与法律、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思考,是一种在宪法秩序内部看待基本权利与部门法关系的视角,可在实践中重视立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然而上述内涵尚未揭示出该命题更为精确的义理,即基本权利与普通法律及其他公权力之关系,故而有必要重新梳理相关概念,以期获得对基本权利具体化较为精当的表述。
一、 从限制到界定:法律保留原则及其扩展
基本权利具体化有广狭之分,与基本权利限制原理的法律保留原则关联密切。法律保留原则的中心内涵是授权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又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基础。早期在谈及基本权利具体化时,其意所指的不过是基本权利的限制。如传统学者在讲授言论自由时,通常会以刑法的侮辱罪、诽谤罪为例,阐明言论自由的外部界限;在讲授自由时,以刑法的禁止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为例,阐明宗教自由所受的限制。刑法规定的诸多罪名是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以法律方式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亦即在否定意义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但是,否定意义上的基本权利限制只是划定了基本权利的外部界限,不仅每一个基本权利规范的本质或者核心构成仍不确定,且其在具体生活领域与生活关系中的表现依然处于模糊之中,有必要在联系这两重内涵的同时,确定具体化的含义。
任何一个基本权利规范都包含着形成、限制与保护三部分内涵,它们在不同层面共同构成基本权利的内容。如此,“具体化”就是一个同“形成”关联密切的概念。在逻辑上,形成有双重内涵,既要说明“是”什么,也要说明“不是”什么。由于普遍意义上的关于“不是”什么已经留给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予以解决,此处只讨论肯定意义上的“是”,即基本权利的形成问题。
形成与具体化并非完全无条件的等同,然而形成的过程却持续包含着具体化。有时,形成与具体化分离;有时,形成与具体化重合。两者关系的阐述须依赖以下几个概念的进一步区隔与界分,这就是“规定”、“形成”与“限制”。特别是在对比的意义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形成”与“规定”、“规定”与“限制”。只有明确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异,与形成重合意义上的具体化的意涵才能渐次清晰,获得明确的图景。
“规定”也可称为“界定”,其与形成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涉及基本权利的限制。德国联邦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认为规定是对基本权利规范从内部进行的限制,也是对基本权利核心领域和实质内容的确定。任何一个基本权利规范都有其固定和明确的内涵,这一内涵明确划定了公权力的界限,是任何公权力都无权染指和侵犯的领域,舍此,基本权利便会空洞化,在对抗公权力的近代宪法原理上失去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限制即为通常所谓的限制保留,是指基本权利从外部施加的界限。联邦拉近了“规定”与“形成”之间的距离,认为“规定不仅可以作为形成,而且可以作为(次要性的)限制而存在”。①以此可以看出,“规定”是一个界于“形成”与“限制”之间的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界定基本权利核心领域的意义上,规定属于形成;在设定基本权利界限的意义上,规定是对基本权利内部界限的划定。那么,何谓“形成”呢?
形成是在另一个层面对基本权利的叙事,其所关注的重心主要是对基本权利核心领域的界定,而非着眼于基本权利的限制,被认为是优先委诸于立法者的任务,要求立法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明确基本权利的内涵。宪法中的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需要由立法予以形成始获得明确具体的内容。例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自由,但每一项自由的具体内涵依然处于模糊与不确定状态,需由普通法律予以规定,这种“规定”既是对基本权利抽象含义的形成,也是对其核心领域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条对上述诸概念一一作出了界定,“本法所称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本法所称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本法所称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 ”。又如,宪法规定保护财产权,但财产权的具体内涵何为,则是需要普通法律予以规定的事情。根据民事法律的一般理论,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与知识产权,而每一项权利的具体内涵都须由法律加以明定,否则,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只能停留在抽象与模糊阶段,此即为基本权利内容的形成。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三款界定物权为“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39条又界定了所有权的概念:“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他如住宅自由中的“住宅”、自由中的“信仰自由”等都需要由立法者通过法律或者法院通过解释进一步明确内涵,形成意义。
形成有三重内涵:一为基本权利的原则与抽象属性;一为基本权利与立法者之间的张力;一为基本权利施加于司法机关以任务。在第一重意义上,基本权利的原则与抽象属性赋予基本权利在整体法秩序中的凌驾地位,要求部门法予以贯彻,该过程即包含具体化,也是形成与具体化之重合之处;第二重意义则关乎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问题,立法者在普通立法中形成基本权利之时须确保不得侵犯其核心领域,即立法者既负有形成的义务,亦不得逾越界限;而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肩负着通过解释法律或者填补漏洞的方式形成基本权利的任务与职责。就形成、限制与规定三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区别而言,形成与限制位于两极,规定则属于一个“跨界”概念。以此而言,形成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涉及宪法与立法者、司法者乃至执行者关系的概念,它包含具体化,或者说具有“具体化”的内容,但不等同于具体化。
在肯定和积极意义上,具体化涉及基本权利的形成;在否定意义上,具体化属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前者是对一个基本权利规范内容的构成与核心领域的确定,是对基本权利内部设定的界限;后者是对基本权利外部界限和范围的划定,这两者俱为界定任何一个基本权利的初步步骤。结合基本权利的保障,广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就是一个指涉基本权利的形成、限制与保护的概念,这也是具体化与形成的不相重合之处。何种情形下具体化与形成重合呢?以男女平等原则为例,该原则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体现既被视为形成,亦被视为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化,这是因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男女依据平等原则享有实际的权利,故曰男女平等原则的形成,而具体化则是男女平等在婚姻家庭这一生活领域和生活关系中有所体现。亦即如果某一基本权利同时在具体的生活领域或者社会关系中获得实质权利内容,可说是具体化与形成的重叠。又以结社自由为例,依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私人获得了结社的权利,但是,私人的结社权利仅为宪法规定或者保障的结社权的形成,个人因此获得了结社自由的可能,但并未使结社自由具体化。对比男女平等原则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体现,结社权只授予了私人结社的资格,结社自由的行使具备了可能,但尚未具体化。因而,狭义的具体化是一个局限性很强的概念,它既要求获得内容——权利——形成,亦要求这一权利内容在一个法律关系——生活领域——生活关系中予以体现。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德国学者将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仅限定在一个极为狭窄的领域中的原因。同时,由于私法关系中一部分基本权利既表现为形成,又以生活关系为依托,故而家庭法中亦有一部分基本权利的形成与具体化重合,这也意味着担负具体化任务的立法者负有受宪法约束,在形成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不得逾越界限,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法院也因此在对形成基本权利的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获得了具体化基本权利的义务或者职责。②
该问题进一步涉及基本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什么是法律?法律之于基本权利的任务与作用?德国学者巴夫厚在研究法律保留原则时,将该原则细化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纯粹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如刑法;二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予以明确具体化的法律,如兵役法,以及实行宪法限制的细则;三是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法律,如财产权之具体内容。这就是著名的法律概念三元化理论。其中第三层意思即法律有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义务最为明显,成为超越限制基本权利与明确具体化宪法界定的基本权利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命题。③德国另一位学者乐雪亦将该问题建立在基本权利与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于1961年提出其观点,认为法律和人权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典型:一是干涉人权的规范;二是澄清人权的规范;三是可以印证人权内容的规范,即形成与实践人权的规范。其中印证规范又分为直接印证与间接印证。直接印证是指法律填补人权的内容,如财产权;间接印证是指由另一个法律形成基本权利的内容,如言论自由须由刑法的限制始获得其内容。④易言之,只有规定诽谤罪、侮辱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才可以从反面获得言论自由的内涵,即只有在刑法规定为言论自由划定的外部界限中,才可以捕捉和把握言论自由的具体内容。在这一层意义上,基本权利存在于刑法所不加限制之处。巴夫厚与乐雪观点的相同多于其差异。其共同之处都承认超越基本权利限制与法律保留原则之外,法律另外具有的细化与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任务,其不同之处仅在于有关对法律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直接印证与间接印证两种区分。因此,从限制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出发,基本权利具体化已发展为“界定”(规定)人权内容的概念。
与早期基本权利须具体化命题的粗疏内涵相比,此处的基本权利具体化有其独特的内涵,即法律具有形成基本权利内容之义务,或曰法律具有“界定”(规定)基本权利内容的任务。何谓“界定”?界定一词并非单纯停留于语义学上,而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内容的再形成。对此,德国另一位学者黑伯乐认为,早期法律概念中认为法律仅在于限制或者干涉人权的含义过于狭窄,且应对这一干涉与限制作宽泛的理解,将其视为对人权的一种“界定”。他认为,立法者在涉及人权的立法时,负有双重任务,即形成人权与界定人权。在他的脉络中,形成人权是填补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界定人权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黑伯乐进一步将两种具体化基本权利内容的法律统统称为“基本权利之实行”,将含有宪法人权的立法视为“执行法”。在他看来,任何在宪法条文内的基本权利都必须有实行性的法律方有实现的可能,故称之为基本权利实行的必需性原则。⑤
基本权利实行概念的提出,开启了法律的一元化时代,由此发展为立法者的任务仅在于诠释宪法。在这个关于基本权利与法律关系问题的思考中,另一位宪法教授hippel完全支持黑伯乐的观点,认为法律保留的全部在于立法者全面考量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及国家需要后,公正地决定人权的界限与内容。其后的另一位教授k·hesse提出了基本权利的内在界限理论,认为立法者的任务在于澄清这些权利在宪法内早已存在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与基本权利限制不同,基本权利的内在界限是指基本权利的核心,其意并非在于限制基本权利,而是清晰化每一个基本权利规范的核心内容,而非基本权利限制意义上人权侵犯或者人权干涉。法律保留的重要性因此大大减退,仅退化为立法者就宪法的人权限制所为之形成立法的诠释作用。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作用也已成为明日黄花,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形成基本权利内容与界定基本权利界限,明确每一个基本权利规范的核心内容。与前一位教授看法不同的k·hesse更是轻视立法者形成人权内容的作用,转而着重于立法者诠释宪法的作用。综合两种观点,法律之于宪法与基本权利的任务与作用,仅在于通过解释宪法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
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其意在通过划定基本权利的外部界限,确保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即内部界限或者范围不受侵犯。基本权利具体化由早期单纯对基本权利设定限制扩展为清晰具体、增加细则与形成内容,在执行或者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意义上,具体化的意旨集中于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界定每一基本权利规范的核心内容。一言以蔽之,广义的具体化是指普通法律对基本权利含义的形成、限制与保护,狭义的具体化是指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明确基本权利的内涵。
二、 积极实施:国家保护义务
法律保留原则之限制基本权利仅着眼于古典自由,即基本权利的防御品质。传统基本权利限制意在防止国家干涉人权的专断,为限制设定限制,其意涵集中于国家尊重人权之一面,基本权利的保护一面尚未充分虑及。同时,随着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兴起及各国国情的发展,基本权利在传统对抗公权力的垂直效力基础上发展了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法律之实施宪法不仅在于界定基本权利规范的核心内容,更发展为国家有义务提供保护免受第三方之侵害。
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根据来源于客观价值秩序。德国学者在谈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了国家权力之于基本权利实施的多面性,这就是保护基本权、具体化基本权内容与限制基本权。“虽然保护基本权是国家权力的任务,而且国家权力可能同时肩负有具体化基本权的义务,同时它也可以被授权来限制基本权”。⑥事实上,保护、具体化与限制同属于广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只不过限制基本权是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古典内涵,形成基本权利内容是发展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国家保护义务则是基本权利具体化概念之于立法权的再发展。⑦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是将一国法律体系视为整体宪法秩序的一种认识。宪法是最高法,具有评价普通法律规范的价值属性;基本权利不仅有主观权利的一面,也不乏最高价值约束下位法的力量,所有部门法有义务在立法中贯彻基本权利价值。除此之外,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尚有制定法上的规范支持,这就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的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
与基本权利限制意义上的具体化相比,国家保护义务之于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在于在私人之间确保基本权利价值的实现,其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涉及基本权利的品质,而且关系到基本权利与立法者关系的问题;除却前述对基本权利品质增加了客观价值层面上的理解,也对基本权利与立法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它不再着眼于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形成,而是着重于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阐释,即立法机关如何积极实施宪法基本权利。在此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并非消极与防御意义上的限制与形成问题,而是一个积极实施问题。
以德国法为例,与美国不同,德国认为胎儿属于宪法上的人,受宪法保护,《基本法》第2条规定了生命权,这就相应地产生了一个胎儿生命权的宪法保护问题。但是,谁来保护及如何保护?适用刑法还是计划生育法?德国社会却存有争论和不同意见。1975年联邦的“第一堕胎案”提供了立法者实施胎儿宪法生命权的阐释。针对议会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的对刑法规定的允许在怀孕的头三个月堕胎的合宪性抽象审查,裁定,国家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刑法保护胎儿的生命。⑧认为,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二项第一句关于“任何人都享有生命与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的规定,可以直接推论出“国家有保护人类生命的义务”, 该条款不仅赋予每个人不允许国家侵害的生命权,国家不能剥夺公民的生命,例如通过死刑,而且“授予国家保护的义务是全面的,它不仅显然禁止国家直接侵害正在发展中的生命,而且明确要求国家保护和助长这一生命,尤其是保护该生命免受第三方的非法侵害”。从的这一推理过程可以看出国家保护义务之具体化的三重属性:一为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一为立法者的积极保护功能;一为国家保护基本权利免受第三方侵害之义务。
“第一堕胎案”提供了立法实施或者具体化基本权利的例证,的判决也引起了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决定保护胎儿生命应由还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第二,究竟哪种法律,刑法还是计划生育法更适合保护胎儿?对于第一个问题,反对者认为采取何种方式保护胎儿生命权是立法者的职责,多数法官超出了自己的职责,判决了一项本来属于议会权力范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妇女的自主决定、医疗委员会的意见,以及与堕胎问题相关的社会讨论与对话。裁决堕胎须征得医生的同意,有权决定堕胎的是医生或者医疗委员会,如果怀孕妇女未征得医生或者医疗委员会的同意而堕胎,其行为就构成犯罪。这样,用刑法保护胎儿将刑事制裁的有害性暴露无疑,对刑事制裁的恐惧阻止怀孕妇女就堕胎问题的公开讨论,反对者认为的主要假设,即刑法及强制性咨询可用于保护胎儿生命被证实是错误的。⑨第一个问题涉及与立法机关的权限划分,第二个问题提供了关于胎儿生命权保护的立法多样性思考。
基本权利限制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在于授权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明确限制的限制,防止立法机关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掏空其内涵,造成基本权利的空心化。消极实施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之具体化亦有其双面性:一是在于由立法机关充实基本权利的内涵或者核心内容;二是通过核心内容的确定确保每一基本权利规范形成一个绝对的法律保留范围,即任何时候公权力都不得进入的区域。两层面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虽然有重大之差异,一个在于限制基本权利,一个在于形成其核心(前者即为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后者即为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或者界限),但二者的着眼点均立足于基本权利防御品质的国家尊重与禁止干涉基本权利的一面上,其意均在于防禁性的,因而是消极的而非积极意义的具体化。
国家保护义务之基本权利具体化与前两者均有不同,它将立足点确立在立法者的作为义务方面,其实质不仅在消极意义上对抗与抵制公权力干预与侵犯基本权利,而且也是在私人之间贯彻基本权利客观价值,因而其效力是由传统基本权利的垂直属性扩张至水平层面,在私人之间实施基本权利。与早期限制意义上基本权利具体化仅在刑事法律规范上有所不同,刑事法律的其他禁止性规范亦属国家保护义务意义上的具体化。前者如侮辱罪、诽谤罪构成言论自由的外部限制,后者如刑法规定杀人罪可视为对宪法生命权的保护,伤害罪可视为对健康权的保护,抢劫罪、盗窃罪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广义上,立法保护基本权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防止私人之间基本权利侵权;二是制定组织与程序规则,确保基本权利的实现。
对比防御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国家保护义务将基本权利的实施由对抗公权力侵害基本权利核心领域之虞扩展至私人,其于生活关系中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基本权的功能大大增强了,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诸项基本权利不仅可以作为对抗公权力的一般性的主观权利,更作为价值通过立法弥散在私人之间,在实证法的意义上渗透于国家的整体法秩序之中。⑩
三、行政权规制:重大性理论
无论早期的法律保留原则、宪法实施之核心内容形成理论,以及国家保护义务,其共同特点是集中于基本权利对立法者的约束(包括不作为与作为义务),探讨法律之于基本权利的任务与作用,其内容均未涉及基本权利之于行政权(执行权)的关系。随着宪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权利具体化又进一步延伸至行政领域。行政权是否负有实施基本权利的义务、如何实施及实施的界限逐渐浮出水面。
通说认为,行政机关受法律约束,但是否受宪法直接拘束在理论与实践中存有争议。但是,基本权利与一般宪法规范不同,其对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具有直接拘束力。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有直接法律效力,并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初看起来,这一规定似乎与《基本法》第20条第三项规定的“立法权受宪法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受法律与法的限制”相矛盾,实则突出了基本权利规范的至上法律效力。原因有二:一是基本权利优越地位是立宪主义理念在宪法规范上的体现,表现为基本权利构成国家权力的界限;二是宪法只初步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分立结构,涉及各机构进一步的权力种类、范围、界限与程序由组织法规定,故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直接依据源于组织法,这也是“依法行政”的原初含义,即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和依据,并由此衍生出行政法上的“授权明确性原则”。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是否拘束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没有明确规定,但序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据此可推断作为宪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约束行政机关,表现为:行政机关可作为违宪主体承担基本权利侵权的宪法责任;抽象性行政行为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不得与基本权利相抵触;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须贯彻基本权利价值;具体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措施、决定与命令须考虑基本权利价值。除此之外,《基本法》第1条第一项规定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以及《基本法》第20条第三项规定的“立法权受宪法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受法律与法的限制”均包含了基本权利之拘束行政权的规范意涵,特别是“受法的限制”之中的“法”,不仅包含了实在法律规范,还包含了超越实在法之上与之外的法规范的约束,这一法规范包含了道德律令与习惯,也是基本权利拘束行政权的规范基础。
侵害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行政权实施基本权利义务的根据。侵害行政下的依法行政与法律保留原则将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执行法律的任务上,行政权不可染指有关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规范形成方面,行政机关不得制定任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具有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规范。但是,积极行政的发展要求国家落实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立法权与之相比显示出相对的劣势,授权立法应运而生,行政机关可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制定有关基本权利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在范围、目的与限度等方面施加约束,立法机关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由此产生了重大性理论,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担负其实施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职责。
重大性理论是指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事项应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予以规范。重大性理论是德国联邦在一个涉及教育立法的合宪性案件中提出的。该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其前提是在承认每一项基本权利均有一个所有公权力之支配均被排除、决不受侵害领域的存在的情况下,允许行政机关以授权立法的方式形成基本权利的内容。这也是羁束行政向裁量行政转变的过程。在羁束行政之下,行政机关是受法律控制的对象,其行为受法律的约束与宰制,更不得形成基本权利的内容,造成对基本权利核心领域的实质侵害。在裁量行政下,行政机关可根据法律授权,在一定范围内制订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具有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则,弥补立法之不足。
重大性理论对于基本权利具体化的意义在于将基本权利之于立法者的责任扩展至行政机关。该理论萌芽甫一出现,学界相当谨慎,认为基本权利核心之不受侵害实可扩大至对抗其他国家权力方面。其理由在于早期基本权利规范主要用以限制立法者的专断与侵害,故尔重大性理论的最初形态仅在于视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为其他国家机关解释时之基准,b11其后逐渐发展到明确执行权受基本权利规范的拘束。重大性理论主要基于三方面内涵:其一,在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内,是否可授权行政机关实施基本权利规范;其二,行政机关在多大的范围与限度内可形成基本权利内容,而不致侵犯基本权利规范的核心;其三,立法机关保持对行政授权的监督,得规范授权立法的内容、目的与限度。
作为行政机关实施基本权利规范、具体化基本权利的内容的观点,重大性理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但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因而遭到学界的不少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一是认为该理论的基础不够明确;二是认为标准不够确定,即认为何谓重大事项无法提供判断;三是对委任立法制度的不信任。所谓理论基础不够明确,在于重大性理论是基于两个原则的混合,即法律保留与法律确定性原则。但是,这两个原则实为两个独立且不同的问题,前者在于由立法机关制定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后者在于要求法律须明确、稳定,具有普遍的效力。法律确定性是形式主义法律概念的固有要求,行政机关的执行性质使其在接受授权制定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规范时有可能冲击法律确定性原则,使其内容的制定逃脱确定性原则的拘束。这将有违法律概念的基本内涵,有损法的权威。对于标准不够确定问题,联邦虽然认为任何国家措施只要是实践人权之重要或重大的涉及自由及平等权即属重大,但是法院自身的标准对此并不一致,且何谓重大不过沦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标准加诸立法者之上,形成立法者的监护人。所以,重大性理论无法满足法律确定性原则的要求,有可能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对于授权立法的不信任问题,反对者的批评实则有些过度。积极行政与裁量行政时期作为补充立法不足之补充,授权立法是时展与人权保障的客观需要,自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空间,只要注意制定的程序、监督与满足法律明确性原则,就有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
四、个案具体化:违宪判断与合宪性解释
司法实施基本权利的本质一是如何落实基本权利之于司法权的任务,二是于具体的生活关系中明确基本权利的内容,促成基本权利的实证与现实化。b12这与传统违宪审查既有交叉之处,也有根本不同。交叉之处在于基本权利的核心不受侵犯以约束司法机关,司法机关需以此为界限判断公权力是否越界;不同之处在于法院需在私法关系中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形成或者具体化基本权利之内涵。前者导致法律保留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个案适用,属于宪法解释;后者导致基本权利效力向水平方向拓展,法院通过对法律的合宪解释具体化基本权利,是对法律的解释。亦即通过司法权力具体化基本权利之内涵实现个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基本权利作为个人防御性的主观权利;二是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作为共同体客观秩序的组成部分。b13第二层含义尤其指明了司法具体化基本权利的前提,即基本权利是被作为客观法价值而非具有请求性质的主观权利而看待的。
法律保留原则的个案应用可分为不同类型。首先,比例原则用于审查和判断系争法律是否构成基本权利核心之侵害。基本权利具体化之于司法主要体现在法院审理宪法诉讼的判决中。比例原则的内容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原则要求法院在审理个案时在案件事实与所适用的法律之间进行衡量,判断法律用以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是否适当或者过度,是否导致基本权利核心被侵害。由于每一个案件的事实不尽相同,在个案中,衡量手段与目的的关联性只能通过法官的解释界定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其次,基本权利规范的抽象性需法官对特定基本权利的内容予以个案界定,进而确定其核心内涵是否受到侵犯。b14以言论自由条款为例,言论自由中的“言论”一词具有模糊性,其内涵着重于“表达”,其价值侧重于“表现”,故而言论自由通常被归于“表现自由”的范畴,但其外延并非十分确定,而具有多义性。特别是随着科技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表达或者表现行为可归入“言论”的范畴。除言辞形式外,出版、集会属于表达行为的延伸;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网络亦从属于表达之列;在否定的意义上,沉默是表达的反向形态;以肢体与行为等方式从事的表达行为被称为“象征性言论”等等。特定形式的表达行为是否被认为属于“言论”构成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需法官在个案中根据案件事实决定。这表明,宪法规范的抽象性需要法官通过解释补充规范内容形成意义。相对于普通法律,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尤为明显,诸多基本权利条款需法院通过解释进一步补充其内容。该过程也是法院通过解释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含义的再形成过程。法官在个案中通过解释界定特定行为是否构成宪法所称的“言论”,是对“言论”意义的再形成,属于具体化之一种。
与立法者形成基本权利与具体化的重合相比,司法形成基本权利更多表现为狭义的具体化,且其是通过解释宪法完成具体化的。法院通过解释确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和内容是在个案中,也是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经由此种解释明确的基本权利是在具体法律关系中获得其内容的。一方面,特定基本权利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持续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内容表现形式并非完全相同。德国学者认为,“基本权自由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样一种自由的内容需要持续不断地被确定,也就是说被限制”。b15它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内容需要不断地被确定;二是限制本身就是对基本权利含义的确定。这与本文所持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定义相一致,即广义的基本权利具体化是一个包括形成、限制与保护三方面内涵的概念,限制既是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也是一个关于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问题。并且,该过程中的基本权利具体化着眼于防御性基本权,因而法院通过解释在个案中对基本权利内涵的持续与再形成既是明确基本权利的内部界限,也是明确基本权利的外部界限即限制,此即为前述所阐明的“规定”之意涵,以此确定法院对立法者是否逾越双重界限进行违宪判断的司法审查标准:立法者是否侵犯了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问题,如果限制超过了必要限度,则可能侵害基本权利之核心领域,在此情形下,法院就违反了过度侵害禁止之原则。亦即只有在划定基本权利核心领域的前提下,才能判断限制是否过度。
合宪解释是普通法院或者民事法院在审理普通案件过程中对法律进行的符合宪法的解释,是一次基本权利价值之光照耀普通法律之旅。法官固然有优先适用法律的义务,但是,特定情形下立法者没有及时履行立法义务,没有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通过立法予以形成,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处于空白状态,法官在审理普通民事案件时负有将宪法基本权利具体化的任务。通过解释法律,法官将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注入其中,这也属于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例如,德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在立法机关尚未制定男女平权法之前,该原则的具体内涵并不明确,民事法院在审理普通案件时通过解释宪法男女平等原则,将该原则的精神渗透至私法关系中,此解释就属于合宪解释,解释的过程既是阐明男女平等原则的内涵,亦是对该原则内容的形成,还是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具体化。又以我国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者享有的劳动保护内涵批复亦属于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明确劳动者的权利内容。1988年10月14日,针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b16该批复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该项权利具有复合性质,既具有防御性质意义上对抗国家干预,谋取工作和职业选择自由的消极属性,亦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提供保护的内涵,还具有科以国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实现的社会权积极属性之义务,当时尚未制定保护劳动者权利和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b17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批复是在缺乏具体法律情况下对劳动合同作出的一次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b18是将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在具体劳动关系中的具体化。
但是,合宪解释具体化基本权利与法律保留原则个案应用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基本权利含义的形成与具体化。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保留原则的个案应用固然可以通过解释宪法对基本权利再形成,但其理论品质着眼于基本权利的防御性质,是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对视的框架之中的一种思考,其所依托的司法哲学是一种消极主义,法官尊重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优先性,不去否决争议法律的合宪性。合宪性解释的理论品质则是在整个法秩序内部,基于基本权利的价值属性以及其相对于下位法的优位属性,其思考框架并非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峙状态,而是如何于具体的生活领域与生活关系中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之内涵,法院对立法者的尊重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缺位情况下对法律依照宪法所进行的解释及内容的填充。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因缺乏普通立法的司法具体化基本权是以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而放射适用于普通法律为前提的,法官在对法律作出符合宪法的解释时所依据的是基本权利的“价值”属性,而如何确定“价值”之含义,依据何种标准具体化“价值”之内涵,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官主观标准与个人偏好的流入,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法官专断,威胁法律的安定性,且“价值”一词模糊或者淡化基本权利防御属性之可能仍是不得不予以警惕和防范的。但是,公认的观点是,对解释基本权而言,当仍然缺乏普通立法清晰化基本权利的内容、具体范围、各项基本权利之间的联系与界限之时,司法通过解释法律具体化基本权利有其必要性,“价值秩序”的思考依然是一种有用的提示与帮助。通过解释,单项基本权利可以获得确定内容,并可避免援引无法解释清楚的“价值”。b19
结 语
纵观基本权利具体化命题的发展脉络,其实质一则在于确定公权力之于基本权利的义务,确保基本权利核心内容不被侵犯,二则在于发挥基本权利的“功能”属性,使基本权的法价值体现于具体的法秩序与生活领域中。前者是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之重心,后者是基本权利的客观法作用。二者的意义相互协调一致,要旨在于通过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基本权利的形成、限制与保护,于共同体整体秩序之内确定个人身份与地位,因而具体化的过程持续负有双重意涵:对公权力的警惕与依赖共存;立法者不仅承担形成与具体化基本权利的义务,也是基本权利的敌人。
同时,虽然意在抵制公权力专断的法律保留已经不是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唯一叙事,于具体生活关系中展示基本权利价值的法律自由同样重要,但这不意味着削弱防御品质的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固有内涵。近代立宪主义决定了抵制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侵犯为其首要使命,宪法关系的原理意在抗衡立法者的专断,基本权利的防御品质仍是需要在基本权利具体化概念中继续加强的一面。亦即无论基本权利之于其他公权力机关的任务在多大范围内被决定,确保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不被侵犯依然是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底线原则。一如德国学者所言,只有当基本权利“作为主观权利的更新现时化成为有生命力的现实之后,其作为客观法的意义才能得以实现”。b20
①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9、250页。
② 前引①。
③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原理》(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④ 前引③,第356—357页。
⑤ 前引③,第357—358页。
⑥ 前引①,第238页。
⑦ 在此,保护、具体化与限制基本权既属于广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同时也是在“具体”与“形成”重合意义上讨论狭义的具体化。
⑧ 参见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577页。
⑨ 前引⑧。
⑩ 德国学者在谈及实证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时,否定基本权利的“天赋”与先国家存在的假设,认为只有基本权利成为实证国家法秩序的内容时,其才能获得保障。“假如不是通过国家来进行法律上的保障、设置与限制,或者没有法律保护的话,那么基本权便无法将一种具体的、现实的自由与平等的地位赋予每个公民个人,也无法在共同体生活中发挥功能,假如基本权缺乏与宪法秩序中的其他内容的关联性的话,它们也无法成为现实……”前引①,第230、231页。
b11 参见陈慈阳:《基本权核心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6页。
b12 德国司法实施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规范基础有二:一是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障它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一是基本法第1条第三项规定的基本权利直接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两者都包含了基本权利对于法院的约束力。除了规范依据之外,司法实施基本权利有三方面的理论基础:第一,基本权利规范的至上属性。基本权利规范在不同国家借助不同理论获得至上地位。德国得益于基本法的明示规定及其后通过判例确立的客观价值理论,英国源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超国家属性。第二,有些国家明确规定法院作为公共机构须遵守基本权利规范。例如,南非宪法、《欧洲人权公约》等都规定,法院作为公共机构负有实施基本权利的职责。第三,法院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法官的职责是适用法律裁决纠纷,法官固然有优先适用法律的权力,但宪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最高规范,法院在裁决普通法律纠纷中需考虑宪法的价值决定,在解释法律时既不得违反宪法,也不得侵害基本权利价值。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法院有实施和遵守宪法的义务。
b13 前引①,第270页。
b14 抽象与原则不同。原则具有不确定性,包含道德与价值判断;抽象是指不具体、含混和模糊不清。针对却伯关于宪法规范特别是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具有抽象性,须补充具体内容而具有原则性的观点,斯卡利亚不予苟同,认为却伯混淆了原则与抽象的区别。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属于抽象而非原则。宪法规范包含许多类似言论自由的抽象条款,但并非意味着它们具有原则属性。斯卡利亚认为原则是带有雄心的条款,具有未来指向性。抽象与一般不等于雄心。他特别反对那种把宪法视为具有雄心和抱负的文件,认为宪法的作用仅在于确保当下和眼前的权利能够得到确实保护;如果眼前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未来也就不能保护。就言论自由而言,用他的话说就是“确保言论自由至少在今天就是确保某些未来,而确保仅仅是未来的雄心等于什么也不确保”。see antonia scalia,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 and the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
b15 前引①,第250页。
b16 最高人民法院[88]民他字第1号。
b17 《劳动法》1994年制定并颁布,《劳动合同法》2007年制定并予公布。
b18 此处之所以将在缺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称为法律解释,是因为法院是对劳动合同有效性的解释。依据民法的一般理论,契约是法律之一种,创设权利义务,称为“契约上的权利或者义务”。西方法谚中亦有“契约须遵守”。
b19 前引①,第243页。
b20 前引①,第239页。
on falsification of specifica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zheng xian-jun
相关文章
互联网保险法律监管探讨 2023-01-05 09:03:53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浅议 2022-12-30 08:29:57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探讨 2022-12-28 09:00:02
数字货币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应对态度 2022-10-11 10:06:39
法律顾问在企业合同法律风险的作用 2022-10-08 15:34:18
高校管理 法律风险 防范 2022-09-30 14:52:54